| | | | 以她之名(精)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小說 -> 科幻小說 | | 【市場價】 | 350-507元 | | 【優惠價】 | 219-317元 | | 【介質】 | book | | 【ISBN】 | 9787540484354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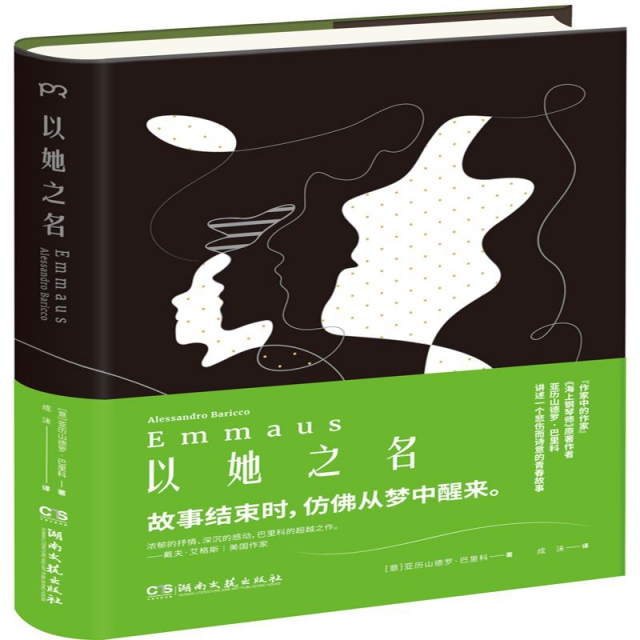
-
出版社:湖南文藝
-
ISBN:9787540484354
-
作者:(意)亞歷山德羅·巴裡科|譯者:成沫
-
頁數:191
-
出版日期:2018-03-01
-
印刷日期:2018-03-01
-
包裝:精裝
-
開本:32開
-
版次:1
-
印次:1
-
字數:88千字
-
-
1. 當代歐洲小說大師、《海上鋼琴師》作者巴裡科的經典作品,被認為是其寫作生涯的**之作。
2. 美國搖滾樂團魔力紅(Maroon 5)主唱亞當·萊文摯愛的小說。他說:”《以她之名》營造的緊張氛圍使我三次將它放下,讓眼睛放松,並做下自我調適。比較之下,我的世界實在平淡,過於標準化了。”
3. 1個女孩,4個男孩,一段危險而詩意的青春故事。濃郁的抒情,深沉的感動,讀完後,仿若從夢中醒來。
-
故事結束時,仿佛從夢中醒來。
《海上鋼琴師》作者亞歷山德羅·巴裡科新作,被認為是體現其至高成就的代表作。
世俗的與虔誠的,富有的與貧窮的,主宰命運的與受命運擺布的——在《以她之名》所述的兩極並存的世界,四個男孩兒被同一個女孩安德雷吸引。他們都來自為生存而奮鬥的家庭,安德雷則屬於另一個世界,並且極度美麗。她刺激著他們去探索,去冒險,經歷性意識的覺醒、近乎病態的抑郁、無邪的天真和對宿命的敬畏。在這股激流之中,四個男孩從青年走向成熟。
-
[意大利] 亞歷山德羅·巴裡科(Alessandro Baricco)
1958年生於都靈。1991年,處女作《憤怒的城堡》獲得意大利坎皮耶羅獎、法國美第奇外國作品獎。1993年,《海洋,海》獲得維多雷久文學獎和波斯克城堡文學獎。1994年,《絲綢》榮登歐洲各國暢銷榜單,2007年被改編成電影,由凱拉·奈特莉主演。1998年,《海上鋼琴師》被知名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改編成電影。2016年,巴裡科以其全部創作榮獲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國際圖書節獎頒發的小說大獎(Marele Premiu al FICT)。
他還是導演和表演者,曾自編自導影片《第二十一課》。
巴裡科的作品有著濃烈的藝術與童話氣質,富有實驗性與音樂感,濃縮了人類美好而溫暖的情感,既古老又新鮮,既傳統又現代。他被美國《圖書館雜志》稱作”作家中的作家”。
在我的小說裡,有很多天真的東西。我說的”天真”是那種沒有被世俗和厭倦污染的東西。我喜歡挑戰那些偉大的作品,我推崇萬古流芳:這是對抗死亡的一種方式。
——亞歷山德羅·巴裡科(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說)
譯者:成沫
羅馬大學羅曼語文學博士,同濟大學中意學院、人文學院教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歐洲中世紀文學、意大利文藝復興、但丁與彼特拉克等。
-
-
正文P027—035
我們上了橋,都給嚇著了。在騎車回家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天色已晚,於是用力地踩腳踏板。我們什麼都沒說。鮑比拐彎回家了,然後是聖托,剩下盧卡和我。我們緊挨著對方,踩著腳踏車,沉默不語。
我之前說過,盧卡是我*好的朋友。我們隻需一個手勢就可以互相理解,有時一個微笑就夠了。在女孩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我倆共同度過了生命中幾乎所有的下午——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有時候可以在他張口之前就說出來。我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認出他,隻要看他走路的樣子——他的肩膀。我看起來比他年長,我們看起來都比他大,因為在他身上仍保留著孩子的某種特征——在他的細小骨骼、白皙的皮膚中,以及在他的臉上——他的臉精致而英俊。他的手、細長的脖子、干瘦的腿也顯得孩子氣。但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我們沒有意識到——如我之前所說,我們很少在意外貌的美麗。我們的世界並不需要這個。就這樣,盧卡擁有美麗卻不利用它——像一場遲到的約會。在很多人看來,他是個給人距離感的人,女孩子們喜愛那種距離,她們稱之為”憂傷”。但是,和其他人一樣,他隻是單純地想要快樂。
幾年前,當我還是十五歲的時候,某個下午,在我家裡,我和盧卡躺在床上看有關F1賽車的雜志——在我的臥室裡。床邊就是一扇窗。窗戶開著,正對著花園。我的父母在花園裡。那是個周日,他們在聊天。我們沒有留神聽,而是看著雜志。但從某一刻起,我們開始留神傾聽,因為我的父母談論起盧卡的母親。顯然,他們沒有意識到盧卡也在那裡,於是談論起他的母親。他們說她是一個十分能干的女人,真是可惜,遭受如此不幸。他們說上帝讓她背負了一個可怕的十字架。我看著盧卡,他微笑著向我示意,讓我不要動,不要弄出聲響。他好像興致正濃。我們在那兒繼續聽著。外面,在花園中,我的母親說,與一個病成這樣的丈夫一起生活一定是件可怕的事,那該會是多麼痛苦的孤獨。然後,她問我的父親治療進行得如何。我父親說他們什麼都嘗試過了,但真相是,他們永遠不會擺脫那些東西。他說,隻能祈禱他不會在某**下定決心擺脫一切。他說的是盧卡的父親。我為他們說的那些話感到羞愧。我回頭看盧卡,他向我示意,像是在說他什麼都沒聽懂,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麼。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腿上,希望我不要動,不要出聲。他想要聽下去。外面,在花園中,我的父親在談論一種被稱為”抑郁”的東西,這顯然是一種疾病,因為與藥和醫生有關。有一刻,他說,這對妻子和孩子來說,真是太可怕了。可憐人。我母親說。她沉默了一會兒,又重復了一遍”可憐人”,指的是盧卡和他的母親,因為他們要與病人生活在一起。她說人們隻能祈禱,要是她,她也會這麼做。然後我的父親站起來,兩個人都站起身,回到屋裡。我們本能地低下頭,把目光移回F1賽車雜志上,害怕房門會忽然打開。但那沒有發生。我們聽見我父母的腳步聲,他們沿著走廊,走向客廳。我們在那裡一動不動,心怦怦地跳。
我們得離開家,但並不順利。我們走到花園,母親出來問我準備什麼時候回來時,發現盧卡也在。她喊出他的名字,好像是在跟他打招呼,但聲音中充滿驚慌——她之後什麼話也沒能說出口,不像平常總能聊上幾句。盧卡轉向她,跟她道晚安。他說得很有教養,用他*平常的口氣。我們在假裝這件事上都異常在行。我們出門時,母親仍在那裡,站在過道上,一動不動,手裡拿著一本雜志,食指夾在書頁中。
我們並排走著,有一陣子什麼也沒說。有什麼藏匿在我們的思想中,我倆都懷有心事。要過街時,我抬起頭,看看有沒有汽車駛來。那一刻,我也看見了盧卡。他兩眼通紅,低著頭。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的父親生病了——縱然奇怪,但事實上,盧卡也從沒有這樣想過。由此可以看出我們是怎樣的人。
我們對父母有種盲目的信心;我們在家裡所看到的都是正常而平穩發展的事,以及代表心態健康的各種禮儀。我們因此崇拜父母——他們把我們從任何不正常中挽救回來。因此不存在這樣的假設——他們自身處於不正常的狀態,比如一場疾病。不存在生病的母親,隻有疲倦的母親。父親從不失敗,隻是偶爾焦躁不安。不幸——我們不願觸及的,時不時以疾病的形態降臨,它們總有個名字,但在家裡我們都閉口不提。
在我們看來,這很正常。
如此,不知不覺間,我們繼承了面對悲劇時的無能,以及對命運的鈍感:因為在我們的家裡,不好的事情是不被接受的,這樣可以拖延那些一旦被觸發就會無限期膨脹的、真真切切的悲劇的發生——我們就是在這樣看似平靜實則危險的沼澤中長大的。這是一塊荒謬的棲息地,由被壓抑的痛苦和每日的禁忌構成。但我們無法意識到這有多荒謬,因為我們是沼澤裡的爬行動物,我們隻認識那一片世界:沼澤對於我們來說是正常的。就這樣,我們消化大量不幸,並把它們當作生活的必然,而不曾懷疑有傷口需要愈合、有破碎的身心需要縫補。同樣,我們忽略丑聞,因為我們出於本能,將身邊人對自己的傷害視為對日常生活不期而至的補充。比如說,在教區電影院的黑暗中,我們感覺到神父的手搭在我們的大腿內側,卻沒有憤怒,而是急忙得出結論——顯然,事情就是如此,神父把手放在那裡,我們不需要在家裡提到這件事情。那時我們十二三歲。我們沒有把神父的手移開。在隨後的星期日,我們從同一雙手中領取聖餐。我們以前能那麼做,現在仍然能——為什麼不把壓抑轉化為優雅,把不幸化為生命中的一抹色彩呢?盧卡的父親從來不去體育館,他受不了擠在太多人中的感覺。我們知道這點,並視之為令人敬重的舉止。我們一直認為他有一種難以言明的貴族氣質,
因為他的沉默。我們一同前往公園的時候,他走路緩慢,不時發出笑聲,就像在做出某種讓步。他從不開車。在我們的記憶中,他從來不抬高嗓門說話。在我們看來,如此種種都是他高貴尊嚴的表現。我們從未察覺在他周圍的所有人都有種獨特的歡樂—確切地說,是勉強的歡樂。我們從未在意,因為我們將這種獨特的歡樂視作一種尊重—實際上,他確實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官員。我們認為他跟其他父親一樣,隻是*難以理解。這麼說吧,*加陌生。
晚上,盧卡坐在他父親的身邊,在沙發上、電視機前。父親將一隻手搭在他的膝蓋上。盧卡什麼都沒說。他們什麼都沒說。時不時地,父親緊緊地抓住孩子的膝蓋。
“那是一種病”是什麼意思?**,我們一起走在路上時,盧卡問我。
我不知道,**沒概念,我說。我說的是實話。
繼續談論下去沒有意義,我們很久很久都不再提起它。直到那天晚上,四人從安德雷待過的橋上回來,*後隻剩下我們兩個。在我家門前,我們停下自行車,一隻腳撐在地上,另一隻踩在踏板上。父母在等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總是在七點半喫晚飯。我得走了,但我能看出盧卡還有話要說。他把身體的重心挪到另一隻腿上,將自行車朝另一側傾斜。然後他說,他靠在橋欄杆上的時候弄明白了一件事——他記起一件事,並且弄懂了它。他稍停了一下,看我要不要走。我留在那裡。在我們家裡,他說,喫飯時總是很安靜。你們家不一樣,鮑比和聖托家也和我們家不一樣,我們家喫飯時是不說話的。我可以聽見所有的聲音,叉子刮盤子,水倒進杯子裡。尤其是我的父親,他一言不發。總是這樣。然後我想起父親有多少次在喫飯時一言不發地站起來——我們還沒有喫完,他便站起來,打開門,走到陽臺上,掩上身後的門,站在那兒,靠在欄杆上,就在那兒。許多年來,他一直這樣。我和媽媽會抓住這個機會——我們會聊天,媽媽會開個玩笑,或站起身拿一個盤子、一個瓶子,或問我個問題,諸如此類。透過玻璃窗可以看見我的父親,背對著我們,有點駝背,俯身在欄杆上。這麼多年來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但**晚上,在橋上的時候,我想到他去那裡是要干什麼。我覺得我父親去那裡是想跳下去。他沒有勇氣這麼做,但他每次起身,都是帶著這個念頭到那兒去的。
他抬起眼睛,因為他想要看著我。
和安德雷一樣,他說。
就這樣,盧卡成為我們中**個越界的。他不是故意這麼做的——他不是個不安分的小伙子。他踫巧待在一扇打開的窗前,大人們不謹慎地說話;然後,他間接地聽說了安德雷的死。這在他——我們——的國度上刻下了裂痕。頭一次,我們中的一個人跨越既定的邊界,懷疑其實並不存在什麼邊界,也沒有避風的港灣。他帶著羞澀的步伐,開始步入無人之境。在那裡,”痛苦”和”死亡”都有明確的意義——由安德雷念出,由我們的父母以我們的語言書寫。他在那片土地上看著我們,等待我們的跟隨。
正文P103—110
我知道這個故事,是鮑比跟我說的,包括所有的細節。他告訴我這些,是想向我解釋,很可能一切早就在發生了,緩慢地發生,宛若地質變遷。但站在山間的石子路上時,他突然間明白,一切都結束了。他指的是我們**了解的某件事情——我們會用不太恰當的方式來形容它:失去信仰。這是我們的夢魘。在前行的每一刻,我們都知道這事如同日食,隨時可能發生——失去我們的信仰。
無論神父給我們多少教誨,關於這件事情,隻有通過*初的信徒的經歷纔能*好地去理解。當時隻有幾個人,耶穌基督身邊的人,在骷髏山上的第二天,把他們的導師從十字架上卸下。他們聚集在一起,驚慌失措。要知道他們身上背負著巨大的悲痛,因為失去了所珍視的,但也僅此而已。那時候,他們中沒有人知道,死去的不是一個朋友、一位先知、一名導師,而是上帝。那是他們當時沒有理解的事。顯然,他們也無法想像,那個人就是真的上帝。他們聚在一起,在那**,在骷髏山後,單純地紀念一個親密的人、一個無可替代的人—他永遠地離開了。但是聖靈從天上降落在他們身上。突然間,帷幕被揭開,他們懂了。與他們一同行走了多年的那個上帝,現在他們認出來了。那一刻,生命中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回到他們的腦海中,帶著耀眼的光芒,深深地照進他們的心靈,直到永遠。在福音書中,那種洞開是由一個美麗的隱喻來形容的:聖靈降身的他們忽然能夠說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一個眾所皆知的奇跡,與先知、占卜者的形像聯繫在一起。這是不可思議的理解力的印記。
因此,按神父的教誨,信仰是個贈禮,來自上天,屬於一個神秘的國度。也因此,它是脆弱的—像是幻覺,也如幻覺一般無法觸摸。它是超自然的。
但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向來遵從教會的信條,但也了解另外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來源於生養我們的溫順的土地。在那兒,我們不幸的家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讓我們繼承了某種無法改變的本能——相信生命是一場無盡的體驗。他們傳遞給我們的習俗越是簡樸,每**,他們從地下對我們的呼喚便越是深遠—呼喚一種無盡的野心,一種期待,幾近毫無理性的期待。從孩童時期起,我們便帶著明確的目的向這個世界靠近,要使它重新歸於偉大。我們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是公正的、高貴的,為了它變得*好而不懈努力,在創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這使我們成為反抗者,成了不一樣的人。世界於我們而言,大體上就是一份枯燥而恥辱的責任,**不符合我們的期望。在那些不信者的生活裡,我們看見應受譴責的日常生活;從他們每一個行為中,我們察覺到那些拙劣的模仿,模仿我們所夢想的美好人性。任何不公——每一份痛苦、惡毒、卑劣、殘酷——都是對我們這份期待的冒犯。沒有意義的道路,每一個失卻希望及高貴靈魂的人,對我們也是冒犯。每一個卑賤的行為。每一個迷失的瞬間。
因此,在相信上帝之前很久,我們就相信人——在*初,這本身就是一種信仰。
像我之前所說的,信仰在我們體內發動了一場戰爭——我們反抗,我們與眾不同,我們瘋狂。他人喜歡的,我們覺得厭惡;他人鄙夷的,我們覺得珍貴。無須多言,這一切讓我們興奮。我們帶著想要成為英雄的想法長大——盡管是奇異的一類,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我們不喜歡**或暴力,或是殘暴的抗爭。我們是陰柔的英雄,漸漸卷入赤手空拳的爭鬥中,滿懷著孩童般的純真,以讓人惱怒的謙虛戰無不勝。我們在世界的齒輪間昂首爬行,但邁著緩慢的步子——就像拿撒勒的耶穌那樣邁出謙卑而堅定的步伐。他在公眾的注視中走過整個世界,在創立信仰的教義之前,首先確立一種行為規範。如歷史所示,誰也無法戰勝他這種行為規範。
在這個顛倒的傳奇史詩的深處,我們發現了上帝。這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我們如此篤信每一個造物,因此自然地開始想像創造—我們以上帝之名稱之為智慧行為。因此,我們的信仰不是充滿魔力的、無法控制的事,而是順理成章的推論,將我們所繼承的本能無限延伸。為了尋找意義,我們漸行漸遠,而旅途的終點就是上帝—完整的意義。這很簡單。我們失去這份簡單時,求助於福音書,因為在那裡我們從人向神的過渡永遠地依照一個固定的模板,反抗的人之子與受寵的神之子合而為一,融會成一具血肉軀體、一位英雄。在我們的世界中可能被看作瘋狂的事,在那裡則是啟示,完結的命運—**的符號。我們從中挖掘出沒有稜角的堅信—我們稱之為“信仰”。
丟失信仰的事時有發生。而當我使用”信仰”這個表述時,並不準確——它仿佛是一種魔法,但與我們無關。我不會丟失信仰,鮑比也不會。我們還沒有找到它,所以不會丟失它。沒有信仰與失去信仰**不同,毫無神奇魔力。在我的腦海中,信仰的丟失就像一面牆的粉碎——結構中的一角脫落,一切因此崩塌。因為石牆是堅固的,但石牆上總有脆弱的連接、不穩固的支撐。時光流逝,我們確切地了解到那一處究竟在哪裡——那是將會出賣我們的隱秘的石子。那裡,就是我們放置英雄主義、宗教情感的所在。在那裡,我們拒*他人的世界,我們所鄙視的世界,帶著出於直覺的堅信;在那裡,我們知道並且聲明,他人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隻有上帝能讓我們滿足,其他任何事都不行。但並不總是如此,並不總是。有時候,我們會滿足於別人一個優雅的舉止,或是迷戀一個美麗的世俗詞語。生命閃光,在錯誤的命運之中;有時候,是罪惡中的高貴在吸引我們。一束光透過,而我們沒有察覺。石子般的堅信破裂,一切隨之傾塌。我在很多人身上看到這個過程,我在鮑比身上目睹了。他跟我說,在我們周圍,有著許多真實的東西,而我們看不見,但它們就在那裡——它們擁有意義,不需要上帝。
給我舉個例子。
你,我,我們是真的存在,並不是在假裝存在著。
再舉一個例子。
安德雷,甚至是她周圍的人。
你覺得那樣的人有什麼意義嗎?
是的。
為什麼?
他們是真實的。
而我們不真實?
對。
他想說的是,在意義缺失的時候,世界仍然繼續。在混亂中存在一種美,有時候甚至是一種高貴,而我們並不了解這些,比如一種我們從未想到過、但切實存在的英雄主義——某種真理的英雄主義。如果你憑著自己的眼睛,在注視著這個世界的時候認出了它,哪怕隻有一次,你便會迷失——於是,你將面對另一場戰爭。在成為英雄的確信中成長,而我們在傳說中被紀念。上帝像是個天真的權宜之計,消失了。
鮑比跟我說,山中的那條石子路,當時在他看來,突然變成城堡的廢墟。**沒有辦法在上面行走,他說。
我們看著他漸行漸遠,但並不是看著他的背影;他的眼睛仍注視著我們,他的朋友們。他還會回來的,不會太久—我們這樣以為,不曾想過會看著他真的消失。但他不再去醫院的瘦鬼那裡或其他地方了——我們曾一起去的地方。他來教堂裡和我們一起演出過幾次,之後就再也沒來。我在鍵盤上彈出貝斯的聲音,但它和鮑比在貝斯上彈出來的根本不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沒有了他,我們的成長變得不同。我們的成長,沒有了他——他的成長有一種輕盈,我們的沒有。
有**,他回來跟我們說起他和安德雷的演出,問我們是不是真的願意去看。我們說,是的。我們去了,而這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譯後記
故事發生在意大利,這曾是一個傳統而又保守的天主教**。小城之中,大家互相認識,每天出門時會友好地打招呼。這是地點的前提。如故事中所說,傳統與守舊的力量仍異常強大,人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固定的攤點買菜,每**去參加教堂的彌撒。與此同時,外面世界的影響開始體現,夜生活、**品,以及性自由。教堂對年輕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弱,流行文化的大潮洶湧而來。這是時代的前提。
年輕人的眼睛沒有錯過任何細節,他們將所看到、聽到和感知到的一切不加分辨地吸收,並視之為生活的常態。他們被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努力遵循父母的生活模板,同時抵抗又擁抱外面世界的**。他們同時面對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必須做出選擇。這樣的選擇讓他們恐懼,迷失了信仰。
那份信仰的根基是意大利天主教,基督教流派中*為保守和根深蒂固的一支。如同原書名“Emmaus”(意為“以馬忤斯”,出自《路加福音》24:13,耶穌基督死後復活並在以馬忤斯向人現形)所揭示,神父、父母向年輕人講解的福音書故事深深刻在他們的心中。每周去教堂聆聽彌撒,參加教區集會,懺悔與禱告,這些習慣的力量有著拯救的作用,讓他們躁動的心獲得平靜。拉撒路的死而復生、聖母的貞潔與母性的光輝、耶穌復活的奇跡,以及他的殉難,拯救了人性,赦免人類的罪惡。如同故事中的“我”所說,年輕人翻閱福音書,尋找著屬於自己的那一頁。借助”繼承而來”的文化與宗教傳統的力量,他們試圖解釋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以及安德雷的存在。
這份宗教信仰構成他們正在成形的世界觀的一半,而另一半則來自一個幾乎**對立的“那些人的世界”——不信者、富人的生活方式和“動物兇猛”的現代文化。與我們的世界裡的年輕人一樣,在這個同樣古老的千年農耕文明中成長的年輕人,面對這個新的、無法解讀的世界時,孤立無援而不知所措。
這就是他們的故事。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