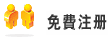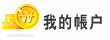A
三十幾年前,也就是20 世紀80 年代上半期,我們在一座小城市演出。一晚,劇團和地方政治團體的一群人在一起喫喫喝喝,長桌的另一端是個跟我一樣紅頭發的女人。一時間,所有的人都開始討論起兩個紅發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他們問著諸如概率是幾分之幾,是否會帶來好運,預示著什麼的問題。
“我頭發的顏色是天生的。”桌子那頭的紅發女人說,既像是抱歉,又帶著得意,“你們看,就像天生紅頭發的人一樣,我的臉上,胳膊上都有雀斑。我的膚色白,眼睛也是綠的。”
所有人轉向我,看我如何作答。
“您頭發的紅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紅色出於自己的決定。”我立刻回復道。
我並不總是這樣對答如流,但這個問題我已經考慮了很久:“對您來說這是天賜稟賦,是與生俱來的命運,對我而言則是自主意識的選擇。”
我沒有繼續下去,以免在座各位認為我傲慢自大。因為,甚至已經有人開始嘲諷和愚蠢地發笑。倘若不回答,沉默就將意味著我甘拜下風:“是的,我的頭發是染的。”那樣他們既會誤解我的性格,還會認為我是個胸無大志的模仿者。
對我們這種紅頭發的後來者來說,頭發的顏色意味著被選擇的個性。一次染成紅色後,我終生都致力於此。
二十五歲上下,我還是個現代的廣場戲表演者,一個激憤但快樂的左派,而非從古老神話和傳說故事中挖掘警世意義的舞臺劇演員。持續三年的地下戀情,*終以年長我十歲的情人的離棄而終結。他是個有婦之夫,一個英俊的革命分子。然而我們在一起激昂地讀書時,多麼浪漫,多麼幸福!事實上,我既生他的氣,也理解他。因為我們的地下戀情曝光,組織裡認識我們的每個人都對我們的事指手畫腳。他們說這會引起妒忌,結果對大家都不好。與此同時,1980 年發生了軍事政變。一些人轉入地下,一些坐船去了希臘,又從那裡逃往德國成為政治流亡者,一些進了監獄遭受酷刑。大我十歲的情人阿肯也在這一年回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身邊,回到他的藥店。而我討厭的圖爾汗——因為他看上了我,還詆毀我愛的人——則了解我的痛苦,並且對我非常好。於是我們結婚了,認為這樣對“革命者家園”來說也是好事。
不過跟另一個男人談過戀愛這件事成為我丈夫的心結。他認為自己因此纔會在年輕人中沒有威信,但卻無法指責我“輕浮”。他並非像我已婚的情人阿肯那樣是個迅速墜入愛河又輕易忘卻的人。因此,他開始難以裝作若無其事。他想像有人在背後說他的壞話,對他奚落挖苦。不久之後,他指責“革命者家園”的同伴不作為,跑去馬拉蒂亞組織武裝鬥爭。我就不講他在那裡試圖喚醒的同胞們是如何揭發這個鬧事者,以及我丈夫是如何被憲兵堵在溪邊挨打的。
短短時間內,生命中這第二次重大失去讓我對政治更加冷淡。有時想著,不如回自己的家,回到退休的省長父親和母親身邊,卻下不了決心。回家,就不得不承認失敗,也不得不遠離戲劇。找個能讓我加入的劇團已非易事。與普遍觀點相反,我想演戲不是為了政治,而是為了戲劇。
我留了下來,於是,正如奧斯曼時期赴前線與伊朗作戰有去無回的騎士們的妻子們,沒過多久我嫁給了圖爾汗的弟弟。事實上,與圖爾加伊結婚,鼓動他成立流動民間劇團是我的主意。就這樣,我們的婚姻一開始出乎預料地幸福。繼兩個失去的男人之後,圖爾加伊的年輕、孩子氣、牢靠似乎成為一種保障。鼕天,我們在伊斯坦布爾、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左派協會的大廳,在無法稱之為戲劇舞臺的會議室裡演出,夏天就去朋友邀請的鎮子、度假城市、軍隊駐地和新建的車間及工廠周邊支帳篷。在飯桌上同時出現我們兩個紅發女人,是這歲月的第三個年頭。這之前的一年,我纔把頭發染成紅色。
事實上,作出這個決定並非出於我身材高挑的考慮。“我想給頭發徹底換個顏色。”那天,我對巴克爾柯伊的中年社區理發師說,但腦子裡連顏色也沒想好。
“您的頭發是棕色,染黃色適合您。”
“把我的頭發染成紅色,”我臨時起意,“這樣會很好。”
我染了一種介於消防車的顏色和橙色之間的紅色。非常醒目,不過包括我丈夫圖爾加伊在內,身邊沒有一個人反對。或許他們想,這是為即將演出的一部新劇做準備。我還注意到,他們把紅色頭發詮釋為我從接二連三的不幸感情中一路走來的結果。那時,他們對我很寬容:“她做什麼都不為過。”
從他們的反應中,我漸漸明白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麼:原版和模仿是土耳其人熱衷的話題。自打酒桌上另一個紅發女人傲慢的否定之後,我不再去理發店用人造染料,開始從市場親手稱重購買指甲草自己染發。這就是跟天生紅發女人相遇的結果。
我特別留意來劇場帳篷的高中生和大學生,率真敏銳的年輕人和飽受孤獨的士兵,對於他們的敏感和幻想誠摯地敞開心扉。他們比成年男人能更快區分顏色的色度,假與真,真情實意與胡話連篇。假使我沒有用親手調制的指甲草染料染我的頭發,或許傑姆也不會發現我。
他注意到我,於是我也注意到他。我喜歡看他,因為他太像他的父親。緊接著,我發現他迷上了我,還觀察我們住的房間窗戶。他很靦腆,我可能是被這一點所感動。不知羞恥的男人讓我害怕。我們這裡有很多這樣的人。無恥是能夠傳染的,因此在這個國家我時常感覺仿佛要窒息。大多數人希望你也能不知廉恥。傑姆斯文、靦腆。他來劇場看戲的那天,走在車站廣場上,他一說出自己的身份,我就明白了他是誰。
我錯愕不已,不過似乎潛意識裡我早已知道他是誰。我從戲劇中學到,在生活中被當作偶然所忽略的東西其實都有某種意義。我的兒子和他父親都想成為作家並非簡單的偶然。三十年後,在這裡,在恩格然,和我兒子的父親相遇並非偶然。我的兒子也跟他父親一樣飽受沒有父親的痛苦並非偶然。我在戲劇舞臺上哭泣多年後成為在生活中錐心痛哭的女人並非偶然。
1980 年軍事政變後,我們的民間劇團也轉變態度,為避免陷入麻煩,淡化了左翼色彩。為吸引人們進帳篷,我從《瑪斯納維》 [1],古老的蘇非派故事和傳說,《霍斯魯與西琳》《凱萊姆與阿斯勒》 [2] 中截取感人場景和對話用作我的小段獨白。不過我們取得的*大成功,是改編自魯斯塔姆和蘇赫拉布故事裡熱淚盈眶的老婦人的獨白。這是為土耳其電影寫悲情劇的一位劇作家老朋友的建議,他說:“不論何時都受歡迎而且抓人心。”
在模仿電視廣告用來插科打諢的表演過後,那些驚嘆於我舞動的肚皮、短裙和長腿從而振奮起精神,說著下流話,或立刻愛上我,或陷入性幻想的所有無恥的男人(甚至包括那些叫嚷著“打開,打開”的*肮髒的人在內),每當我在舞臺上發出蘇赫拉布的母親塔赫米娜看到丈夫殺死兒子時的尖叫,頓時陷入一片深沉可怖的寂靜。
就在此時,我先是幽咽地,緊接著開始撕心裂肺地慟哭。哭泣時,我能夠感受到自己在人群中的力量,我為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獻給表演感到幸福。舞臺上我穿著開衩的紅色長裙,戴著老式珠寶,腰上束著軍用寬腰帶,手腕上戴著那個年代的手鏈。當我在舞臺上帶著母親的悲痛哭泣時,深刻感受到在座的男人們內心的顫抖,眼睛的濕潤和罪惡感的淪陷。從打鬥伊始魯斯塔姆抓住兒子的動作裡我便明白,大多數年輕、憤怒的鄉下佬們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置身於蘇赫拉布,而非強壯、專橫的魯斯塔姆的位置,直覺告訴我,他們其實在為自己的死流淚。不過為了讓他們能夠為自己而哭,首先需要他們的紅頭發母親在舞臺上毫不遮掩地哭泣。
我也目睹,在經歷所有這些深刻的痛楚時,相當一部分崇拜者的眼睛盯在我的嘴唇、脖子、乳房、雙腿,當然還有我的紅色頭發上,哲學的痛苦與性的欲望正如古老神話中那樣彼此交織。看到自己成功地通過每一次轉動脖頸,每一個全身躍動的步伐和每一個眼神,既向觀眾們的理智和情感,又向他們年輕的肉體吶喊,這樣的時刻是美妙的,但我不能常常經歷這樣的時刻。有時,一個年輕男子大聲哭泣傳染了其他人。彼時,一人鼓起掌來,我的聲音含糊不清,雙方爭執起來。有幾次我看到帳篷裡人群的瘋狂,放聲號哭者與暗自涕零者,鼓掌者與咒罵者,起身叫喊者與默默端坐觀看者相互攻擊。大多時候我喜歡並渴望這種興奮和激情,但又懼怕群體的暴力。
不久,我找到另一個劇目,可以與塔赫米娜哭泣的一幕相媲美。先知易卜拉欣,為向真主證明自己的忠誠準備割兒子喉嚨時,我既扮演了在遠處默默哭泣的女人,又扮演了手拿玩具羊而來的天使。不過這個故事裡沒有女人的位置,我沒能感染觀眾。之後,我重新改寫了俄狄浦斯的母親伊俄卡斯忒的話用作獨白……兒子誤殺父親的故事不會激發太多熱情,但作為一種觀念而引發關注。或許,如此足矣。倘若我從未講述後來兒子與紅發母親同床共枕就好了。今天我可以說,這帶來了阨運。圖爾加伊警告過我。然而,不管是他,還是彩排中問“大姐,這是什麼呀?”的送茶人,抑或暗諷“我不喜歡這個”的主管優素福,我都充耳不聞。
1986 年在居杜爾鎮,紅頭發的我扮演了俄狄浦斯的母親伊俄卡斯忒,獨白中講述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兒子上床,我發自肺腑地哭泣。第1天,我們接到恐嚇,第二天半夜,劇場帳篷燒了起來,我們立刻趕到那裡好不容易把火撲滅。一個月後,在薩姆松海邊的貧民區附近搭的帳篷,就在我演繹俄狄浦斯母親的獨白後第二天早上,便遭遇了孩子們雨點般的石子攻擊。在埃爾祖魯姆,懾於憤怒的民族主義青年們對“希臘劇”的指責和威脅,我沒能踏出旅館半步,帳篷則有勇敢正直的警察們保護。我們正思忖,或許鄉下人對直白的藝術還沒做好準備時,在安卡拉的進步愛國者協會裡散發著咖啡和拉克酒味的小舞臺上,我們的劇上演還不過三次,便以“違背人民羞澀和質樸的情感”為由被叫停。在我們的國家男人們彼此*常說“操你媽”這樣的髒話,檢察官的判決不可謂不合理。
二十五歲左右,我還愛著我兒子的爺爺阿肯時,跟他探討過這些話題。我的情人半詫異、半難為情地回憶並笑著對我重復男人們在初中、高中、軍隊裡學到的我從不知曉的髒話,說聲“惡心!”,繼而展開“女人受壓迫”的大話題,說到達工人階級的天堂,所有這些肮髒就都會結束。我應該耐心,為革命支持男人們。不過,千萬不要以為我會進入土耳其左派有關男女不平等的話題。我結尾的獨白不僅僅是憤怒,同時也應當是詩意的和優雅的。我希望我兒子的書裡也能有這樣一種氣質,人們在書中也能感受到在舞臺上看我表演時的這種情感。是我建議我的恩維爾寫一本書,把我們的經歷編成故事,從他的父親、爺爺開始講起。
事實上,為了不讓我的恩維爾喪失掉內心的善良和人性,不學習男人的丑惡,我想過小學階段不送他去學校,自己在家教育。圖爾加伊對我的這些幻想不屑一顧。我們的兒子開始在巴克爾柯伊上小學後,我和圖爾加伊就放棄了戲劇,在迅速普及的譯制片中做起配音。那些年我們去恩格然的理由是瑟勒· 西亞赫奧盧。即使左翼的、社會主義的熱情褪去,我們仍舊跟老朋友見面。很多年後,他讓我們在恩格然再次見到了馬哈茂德師傅。
我們的兒子恩維爾喜歡聽挖井人馬哈茂德師傅的故事。我們一起去拜訪他,他家後院有一口非常漂亮的井。馬哈茂德師傅靠著在第1口井裡找到水後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建設中挖井發跡,他早年間買的地皮迅速漲價,因此過得很寬裕。恩格然人給他介紹了一位帶著一個孩子的漂亮寡婦,她的丈夫去了德國再沒回來。馬哈茂德師傅接受了這個孩子,作為父親盡職盡責。恩維爾和這個孩子——名叫薩利赫——成了好朋友。我費盡心思想讓薩利赫喜歡上戲劇,卻沒能成功。不過我的年輕劇團成員大多都是我從恩維爾的朋友,恩格然的青少年中挑選的。因為恩維爾,我得以時常踏足恩格然。戲劇的熱情是可以傳染的。這些孩子大多在馬哈茂德師傅家裡出入。馬哈茂德師傅在散發著金銀花氣味的自家院子裡也挖了一口井。為避免院子裡玩耍的孩子們掉下去,他在鐵制井蓋上加了掛鎖。但我還是會走到二層小樓的陽臺,看著後花園對孩子們喊道:“別靠近井!”因為古老神話和傳說中的事情*終會在你們身上應驗。你讀得越多,對那些傳說越是篤信,它就越是靈驗。事實上,因為你聽到的故事會在你身上應驗,所以纔稱之為傳說。
是我帶頭把馬哈茂德師傅從井裡弄了上來。前一晚,我的高中生情人在喝了一杯庫呂普拉克酒,笨拙地跟我做愛讓我懷孕後(我們倆誰都萬萬沒想到會這樣)向我傾訴了一切(用他的話說)。說他的師傅十分為難自己,他想回家,回到母親身邊,他不相信井裡能出水,他留在恩格然不是為了打井,而是為了我。
第二天中午,在車站廣場看到他手裡提著小行李箱、驚慌地跑向火車時,我腦子亂極了。來帳篷看我演出的一些男人不僅僅是愛上我(短暫的一段時間),更被極端的嫉妒迷了心竅。
我哀嘆,很可能再也見不到傑姆了。他很少對我提到他的父親,或許打那天起他已經察覺到了什麼。我們也將坐下一班火車離開,但我不明白傑姆為何突然像罪犯般倉皇地逃離恩格然。車站的人群中有手裡提著籃子前來趕集的農民和孩子。之前一天的晚上,圖爾加伊在學徒阿裡的幫助下找到馬哈茂德師傅並把他帶來看戲。馬哈茂德師傅來到帳篷靜靜地觀看演出,彬彬有禮。我們的人也知道阿裡不再是學徒,雇主也停了工錢。我們感到奇怪,派圖爾加伊去了上面的平地,火車也錯過了。然後,就像古老神話中講的,我們一起去了井邊,向下看,之後被我們放下井的阿裡把半昏厥的馬哈茂德師傅弄了上來。
他們把師傅送進醫院。後來聽說折斷的鎖骨還沒完全愈合,馬哈茂德師傅又開始挖起井來,至於他找誰當徒弟,誰資助了他,這些細節不得而知,因為我們的劇團也離開了恩格然。我想要忘記在那裡跟一個高中生在戲劇的意猶未盡中發生了一夜情,想要忘記其實我愛的是他的父親,但那份愛也已經冷卻。還不到三十五歲,我就了解了男人的驕傲、脆弱和他們血液裡的個人主義。我知道他們會殺死自己的父親,也會殺死自己的兒子。不論父親殺死兒子,還是兒子殺死父親,對於男人來說是成就英雄,而留給我的隻有哭泣。或許我應該忘掉自己知道的這些,去別的地方。
[ 1 ] 《瑪斯納維》:伊斯蘭教蘇非主義哲理訓言長篇敘事詩集。
[ 2 ] 《凱萊姆與阿斯勒》:著名的土耳其民間愛情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