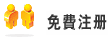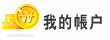A&P
三個隻穿著遊泳衣的姑娘走了進來。我站在三號收銀臺旁,背對著門,所以等她們走過放面包的櫃臺時纔看到。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個穿著綠色方格兩截遊泳衣的姑娘。她是個胖乎乎的女孩子,皮膚曬得黑黝黝的,臀部肥大,顯得柔軟可愛。兩彎白色月牙形印記正好位於臀部下端和腿窩的上面,那裡好像是日光永遠踫不著的地方。我站在三號收銀臺旁邊,一隻手放在一盒艾爾霍牌餅干上,忘了是不是已經把這盒餅干的金額打在收銀機上了,於是,我隻好又在機子上打了一次,這可把那個顧客氣壞了,罵得我無地自容。她就是那種死盯著收銀機不放的顧客。這個老妖婆顴骨上抹著胭脂,大約五十歲,眉毛光禿禿的,我知道她存心要找我的碴兒來消磨日子。五十年來,她都是這樣盯著收銀機過來的,可能還從沒抓到過把柄呢。
我好不容易把她的羽毛捋順了,把她買的各種可口食品裝進袋子——她從我身邊走過去時衝我輕輕哼了聲。如果生逢其時,她肯定會被活活燒死在塞勒姆山的——就在我打發她上路的工夫,三個姑娘已經繞過面包櫃臺轉回來了,她們也沒拿手推車,沿著道道櫃臺,順著收款臺和特種商品箱之間的過道,朝我這邊走來。她們甚至都沒有穿鞋子。其中就有那個身穿兩截遊泳衣的胖姑娘——鮮綠色的泳裝,乳罩上的線縫都還是嶄新的,裸露的肚皮依然很蒼白,我琢磨,這套泳衣她可能剛買來不久——就是這個姑娘,長著一張緋紅的圓臉蛋,鼻子底下兩片嘴唇緊緊地抿在一起。還有一位高個子的,頭發烏黑,但卷得不是很得體,正對著眼皮底下有塊曬斑,她的下巴顯得長了些——你知道,這種姑娘的長相往往在別的姑娘看來顯得非常“惹人注目”和“嫵媚動人”,但其實並不真心這樣認為。她們很清楚,正因為這樣,大家纔那麼喜歡她——然後是第三個姑娘,身材不算太高。她是皇後,看樣子是三個人中領頭的,另外兩個姑娘老在東張西望,扭捏作態。皇後沒有這樣,這位姑娘目不斜視,隻是挪動著兩條著名歌劇女主角那樣白皙的長腿,慢條斯理地朝前走著。她走過來時,腳跟略微用勁,看上去好像並不經常光腳走路,而是先用腳跟著地,接著又把全身的重量移到腳尖上,仿佛每走一步都是在試探地板的承受力,對地面施加一份額外的壓力。你永遠拿不準女孩子的心思(你真的以為她們在用心思盤算著什麼嗎?說不定無非就像關在玻璃罐裡的蜜蜂在嗡嗡亂叫呢),不過,你可以想像,一定是她說服另外兩個姑娘上這兒來的。現在,她正在向她們做示範——挺直身板,邁動步子時從容不迫。A和P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茶葉總公司的簡稱,這裡指該公司開辦的超市。
她身穿一件暗紅色的——也許是米色的,我也說不準——遊泳衣,上面布滿星星點點的小結頭,最讓我驚訝的是泳衣上的兩根弔帶從肩上歪下來,松弛地掛在冰涼的胳膊上端,我猜想,這麼一來,那件泳衣肯定向下滑動了一丁點兒,所以,泳衣上端明顯露出一圈亮閃閃的邊痕。要不然,你簡直無法想像還有比這姑娘肩膀更白的皮膚。由於泳衣的弔帶落下來,從泳衣上端到頭頂,除了她的肉體,就一無所有了——從肩骨以下到胸脯的上半部,這片赤裸白淨的皮膚,看起來就像一張凹凸起伏的金屬薄片,在燈光下閃閃發亮。照我看,這實在是太美了。
她的頭發本來是棕色,由於日光暴曬和海水浸染,已漸漸褪色,挽成圓鼓鼓的發髻,顯得有些蓬松,她的臉看上去有那麼點一本正經的樣子。我覺得,你穿著弔帶松弛的遊泳衣,走進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場,自然隻能板著這種臉了。她高高地仰起腦袋,以致把白皙的雙肩上伸出的脖子拉得格外長,不過,我可一點兒不在乎這個。脖子伸得越長,她就越招人注意。
她眼角的餘光一定感覺到我的存在了,越過我的肩膀,也一定看到了站在二號收銀臺旁,一直張望著她們的斯托克西,但她根本沒有惠顧我們。這位皇後完全沒有注意我們。她的眼睛不停地掃視著排排貨架,然後站住,非常緩慢地轉過身來,這種姿態惹得我心癢難撓。隻見她和另外兩個姑娘低聲細語了片刻,那兩個姑娘因為跟她擠在一塊兒商量過了,顯得舒坦自如了,接著三個人全都順著過道依次來到貓狗食品櫃臺、早點面食櫃臺、通心粉面食櫃臺、米粉食品櫃臺、葡萄干櫃臺、調味品櫃臺、果醬黃油櫃臺、細條面食櫃臺、果汁櫃臺、餅干櫃臺和家常小甜餅櫃臺。我從三號收銀臺旁邊順著這條過道,一眼望到肉類櫃臺。我一路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那個皮膚有點黑的胖姑娘拿起小甜餅,略微想了下又放回貨架。這時,正好有一批顧客推著貨籃車沿著過道走來——這三位姑娘卻逆著人流朝前走去(我們這兒沒有設單行路標或別的什麼標志)——在人群中引起騷動。這些人刮擦到我們這位皇後白淨的肩膀時,你瞧瞧他們的表現,有的抽搐了一下,有的人跳了一下,有的打了個嗝兒,不過他們很快就毅然收回目光,盯著自己的籃子,繼續推著車往前走。我敢打賭,你要是在我們大西洋—太平洋超市引爆一枚炸彈的話,這些人還會照樣漫不經心地伸手從貨架上取下麥片,然後在購物單上劃去麥片,嘟囔著說:“讓我瞧瞧,還有一樣東西沒買呢,打頭的字母是‘A’,是蘆筍,噢,不對,沒錯,是蘋果醬!”或者不管什麼,他們總要嘮叨一番。不過,毫無疑問,這次可讓他們喫了一驚。有幾個別著鬈發針的家庭主婦,甚至把貨籃車推過去後還扭過頭張望了一下,想證實她們看到的景像確實沒搞錯。
你知道,要是在海灘上看到一個穿泳衣的姑娘,那是另外一碼事兒,在那種地方,陽光刺眼,誰也不會互相打量個沒完,可是在大西洋—太平洋食品超市這種涼爽的地方,在熒光燈的照耀下,面對琳瑯滿目的貨架,她卻光著腳在綠色和奶油色的方格橡皮彈性磚地上,大模大樣地逛來逛去,那又當別論了。
“噢,我的爹,”站在我身旁的斯托克西說,“我可真有點發暈了。”
“親愛的,”我說,“使勁攥緊我吧。”斯托克西結過婚了,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相當於在飛機殼上劃過兩道標志,可是據我所知,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他今年二十二歲,而我到今年四月纔滿十九歲。
“過去了嗎?”這位主事兒的已婚男子總算能張口說話了。我差點忘了說,斯托克西自認為將來總有飛黃騰達的一天,也許是在一九九年吧,他會成為名叫大亞歷山德羅夫彼得洛希基茶葉公司或別的什麼商場的經理。
他的意思是我們這個鎮子離海邊有五英裡,海角上有個避暑勝地,而我們的商場正好位於市鎮的中心,女人們從汽車裡面出來到街上時,總穿著襯衫、短褲之類的東西。雖然她們都是些有六個孩子的女人了,腿肚子上像地圖般布滿了暴起的青筋,沒有人,包括她們自己,會在乎這些的。我已經說過了,我們的超市正好位於市鎮的中心,如果站在超市的正門口,你就能看到兩家銀行、一幢公理會教堂、一個報攤和三個房產辦事處,還有大約二十七個混飯喫的老雜務工,在挖中央大道的路面,因為下水道又壞了。我們又不是貌似生活在好望角上;我們是在波士頓市北面,鎮裡有些人已經有二十年沒見過大海了。
這時姑娘們已經到了肉類櫃臺旁邊,在向麥克馬洪打聽著什麼,他用手指了指,她們也指了一下,然後就消失在堆成金字塔般的健樂牌桃子後面了。這時我們隻看到老麥克馬洪輕輕地撫弄著自己的嘴巴,目光追隨著她們,打量著姑娘的關節;可憐的孩子們,我開始為她們感到惋惜了,她們也無可奈何。現在,到了這個故事令人傷心的部分,至少我們家人覺得傷心,不過我自己並不覺得多麼傷心。今天是星期四下午,超市裡空蕩蕩的,我們除了靠在收款機旁,等候姑娘們再次露面外,沒有太多的事可干。整個店面就像一個彈球機,我不知道她們究竟會從哪條過道冒出來。一會兒,她們就從遙遠的過道那頭走了出來,隻見幾個姑娘圍著電燈泡、加勒比海六人合唱隊和托尼·馬丁等這種你會納悶簡直是浪費材料的廉價唱片、六塊一盒的糖果條,以及連三歲小孩看看都會散架的玻璃紙裝的塑料玩具,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轉來轉去。她們又繞了回來,還是那位小皇後領頭,手裡拿著一個灰色的小罐子。從三號收銀臺到七號收銀臺,當時正好沒人值班,隻見她在斯托克西和我兩人間猶豫著,可是,斯托克西總是那麼走運,吸引來一個穿著灰色大寬褲的老家伙,手裡拿著四大罐菠蘿汁,蹣跚地朝他走去(我經常暗自納悶,這些老癟三要那麼多菠蘿汁究竟干嗎用呢),於是,姑娘們就朝我這邊走過來了。小皇後放下那個灰色小壇子,我用手指提起來,壇子很涼。這是王魚牌美味純酸奶油快餐鯡魚:四角九分錢;現在她雙手空了,既沒戴戒指,也沒戴手鐲,光溜溜的就像上帝剛剛造出來,我很好奇,她的錢會從哪兒出來呢?她的表情依然很正經,從那件滿是小結頭的粉紅色泳衣上端正中的凹縫裡掏出一張疊起鈔票。這時,我感到手裡提著的小壇子變得沉甸甸的。我心想,她可真聰明。
大伙兒的好運氣很快就完了。倫蓋爾為停車場上一卡車卷心菜討價還價了半天,然後走進來,正要匆匆走進那個成天藏在裡面的經理室時,突然看到那三個姑娘。倫蓋爾為人極其干巴古板,平時還在主日學校之類的地方教點兒課,可這幾個姑娘偏就是沒逃過他的眼睛。他走過來,衝著她們說:“姑娘們,這裡可不是海灘。”
小皇後的臉上泛起紅暈,雖然那可能隻是臉上的一塊曬斑,她現在離我很近,我這纔第一次注意到。“我媽讓我來這兒挑壇快餐鯡魚。”她說話的聲音讓我有些喫驚,先見到人,後聽到她說話的聲音,常常會有這種感覺的,發音是這樣平淡、低沉,但是在吐出“挑”和“快餐”這兩個話音時又顯得那麼優雅。剎那間我順著她的話音,仿佛偷偷溜進她的起居室。她父親和另外幾個男人,穿著乳白色的外衣,打著蝴蝶領結,在起居室裡圍成一圈站著,幾個穿涼鞋的女人從一個大玻璃盤裡拿牙簽挑出快餐鯡魚。他們手裡都舉著酒杯,品嘗著泡著橄欖和薄荷葉的帶顏色的酒。我父母要招呼客人的話,頂多喝點兒檸檬水,就算踫上真正高興的事,也隻是用刻著漫畫的大玻璃杯喝點希裡茲牌啤酒。
“當然可以,”倫蓋爾說,“不過,這裡可不是海灘。”他老重復這句話實在叫我感到可笑,好像他是剛知道這裡不是海灘。這些年來,他一直覺得大西洋—太平洋超市不過是個大沙丘,他自己就是個救生員的頭兒。他對我的微笑感到不快——我說過,幾乎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但這時他正全神貫注,拿出主日學校監督人的派頭,盯著那三個姑娘。
小皇後臉上的紅暈已經不是曬斑,那個穿方格泳衣的胖姑娘,我更喜歡她的後背——多可愛的臀部啊——尖聲說:“我們不是來商場逛的,我們是來買樣東西的。”
“這沒什麼區別,”倫蓋爾告訴她,我從他的眼神裡可以看出,這之前,他沒有發現這位姑娘是穿著兩截遊泳衣的。“我們隻是要你們到這兒來時穿得體面些。”
“我們很體面。”小皇後突然開口說,她的下唇噘起來,明顯惱火了,想起自己的地位來,相形之下,經營超市的這伙人根本算不了什麼。她那深藍色的眼睛裡閃耀著美味快餐鯡魚的光澤。
“姑娘們,我可不想跟你們爭吵。下次再來這兒,把胳臂擋著點。這是我們的規矩。”倫蓋爾說完轉身就走。那隻是為你立的規矩。當老板的纔需要這樣的規矩。有些人要的卻是少年過失罪。
其間,顧客們推著貨籃車走過來,可是,你知道,這些綿羊般的顧客看到這幕情景時,把斯托克西團團圍住,他用削桃子般輕柔的動作張開一個紙袋,不想漏掉一句話。在這片寂靜中,我感覺每個人都很緊張,尤其是倫蓋爾,他問我:“薩米,你把她們的錢結了沒有?”
我想了想說:“沒有。”不過說真的,我根本就沒想過結賬的事。我按了下結算盤,雜貨,總共四角九分——這事遠比你想的復雜。如果你干得多了,結算盤發出的聲響會構成一支小小的樂曲,照我的心情來領會,聽上去仿佛是在說:“喂(嘭),你們(鏗)這些快活的年輕人(咔嚓)!”——裝零錢的抽屜隨著咔嚓一聲滑了出來。你們可以想像,我輕柔地壓平那張鈔票的皺褶,要知道,這張鈔票可是從我所知道的最柔滑的香草冰激凌似的酥胸中間掏出來的啊!我把五角一分錢放到她那纖小的粉紅色手掌裡,把快餐鯡魚輕輕裝進食品袋裡,把袋口捻在一起遞給她,我在做這些動作時,心裡一直在想著那件事兒。
姑娘們急匆匆地想離開商場,誰又能責怪她們呢?我忙衝著倫蓋爾說了句“我不干了”,說得那麼匆忙就是想讓她們能聽到,希望她們會停下腳步看看我,這位出其不意的好漢。可她們徑直朝電眼走去,店門開了,小皇後、方格子,還有那個相貌平庸的高個子(不過打扮下還是很不錯的)匆匆穿過停車場,鑽進她們的汽車,把我和眉毛緊蹙的倫蓋爾撇在那裡。
“你剛纔說什麼來著,薩米?”
“我說我不干了。”
“我想你是這麼說的。”
“你根本就沒必要讓她們難堪。”
“她們纔讓我們難堪呢。”
我脫口來了句莫名其妙的話。這是我祖母常說的一句話,我相信,她聽了會高興的。
“我認為你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麼,”倫蓋爾說。
“我明白,”我說,“你纔不明白呢,”我從後背解開圍裙的扣結,然後從肩膀上抖下來。幾個朝我這邊的收銀臺走過來的顧客像豬圈裡受驚的豬那樣,互相踫撞起來。
倫蓋爾嘆了口氣,裝出很有耐心的樣子,看起來蒼老肅穆。他是我父母多年的老朋友。“薩米,你這樣做可對不起你爸媽,”倫蓋爾對我說。這倒是真的,我對不起。可是我好像覺得,一旦著手某種舉動了,如果不把它干到底會要了命的。我疊起圍裙,口袋上方用紅線縫了個“薩米”,把它放到櫃臺上,又把蝴蝶結摘下來,放到圍裙上面。沒什麼可奇怪的,這個蝴蝶結本來就是他們的。“你會為這事後悔半輩子的,”倫蓋爾說。我自己也知道這話不假,不過想到他讓那個漂亮姑娘臉紅這事兒,我心裡就感到很別扭。我按了下“停止售貨”的鍵盤,機子隨著“呸普”一聲推出抽屜。這件事發生在夏天倒也不壞,我可以一走了之,用不著慌裡慌張到處去找什麼外衣、橡膠套鞋之類的東西。我穿著頭天晚上媽媽熨好的白襯衣,漫步走到電眼前,店門自動打開了,外面,燦爛的陽光灑滿柏油馬路。
我四處張望尋找我的姑娘們,可她們當然早已無影無蹤了。街上空空蕩蕩的,隻有一個結了婚的年輕女人,在深藍色的鷹牌面包車門旁,正衝著她的孩子尖聲叫罵,責怪他們沒有買到糖果。越過商場外人行道上堆放的袋袋肥料和鋁制的輕便家具,回頭望過去,在玻璃窗裡面,倫蓋爾站在我原來的那臺收銀機旁邊,正跟綿羊般的顧客們結賬。他臉色陰沉嚴肅,脊背僵硬,好像剛注射過一針鐵劑似的。想到日後在這個世上的艱難處境,我的心情頓時嚴峻起來。
醫生的妻子
“鯊魚來了?”醫生妻子灑滿雀斑的鼻頭在水花四濺的空中顯得更加尖削。她的眼睛剎那間因為思考而變得黯然無色,幾乎全部被加勒比海的綠色占據了。水平面在切割著她的喉嚨。“沒錯,有幾條在跟我們周旋。而且,還有幾個又大又黑的家伙正跟隨過來。”
拉爾夫本來漂浮在她旁邊,靠浮力蹲著,這時直起身來,水花四濺,他想測測自己周圍綠色海水的深度。他突如其來的動作把身邊的水都攪渾了。醫生妻子令人驚訝的年輕的笑聲如銀鈴般響徹不絕。
“你們這些美國人啊,”她說,“就是太神經質了。”然後得意地又朝大海深處扎進去一些,當海水在嘴角周圍輕輕冒泡時又漂了回來。她臉蛋小巧,遍布雀斑,在這樣的天氣裡泛著玫瑰色;糾結的褐發被每日的海水浴弄得暗淡無光。“它們很少出現在這麼遠的地方,”她說,向上側著臉,對著天空講著。“隻有在捕殺海龜的季節,血腥會吸引它們過來。我們夠幸運的。我們的沙灘暴露得越來越淺了。這個時候,在聖馬丁那邊,近海岸的水仍然很深,他們肯定得當心。”
她轉過身來,用一個懶懶地漂遊著的胖女人特有的漫不經心的拍打動作,衝他微笑著遊過來。“真不好意思,”她說,因為想使勁卡著喉嚨讓嘴唇空閑下來,聽上去聲音很緊張。“維克·約翰遜來了。他是個非常可敬的人。那位聖公會的老牧師。”她發牧師這個詞的音時非常刺耳,也許是想顯得幽默些。她站在拉爾夫身邊,手朝地平線方向指著。“瞧,”她說,“他過去經常遠遠地遊到這個海灣裡來,他會帶著那條叫鉤子的大黑狗過來。維克會遊個不停,除非一塊肌肉都動不了,然後纔會漂流,抓住鉤子的尾巴,狗會把他拖回去。說實話,那情景可真有看頭,這個肥胖的英國老紳士,白發上水淋淋的,抓著狗尾巴遊回來。他從來不顧忌鯊魚。噢,他會一路遊出去,直到變成一個小圓點。”
他們站在齊腰深的海水裡,拉爾夫先動了起來,然後兩人一塊兒朝海岸方向走去。平靜溫暖的水隨著他們的步伐不斷往上濺。她在拉爾夫旁邊顯得很嬌小,說話時聲音衝著他的肩膀尖叫。“他走了,我真難過。”她說,“是個很可愛的老紳士。在這裡住了四十年。他很愛這個小島。”
“我明白他為什麼要走,”拉爾夫說。他轉過腦袋想欣賞一番沙灘附近這片月牙形的風景,仿佛透過他清新的雙眼,醫生的妻子就會有煥然一新感——他似乎鬧不明白哪部分需要煥然一新——對這個小島之美的感覺。白色的沙灘空空蕩蕩。當地人隻是把它當成一條小路來用。他們的家園坐落在參差不齊的海葡萄籐圍籬的後面,這道圍籬給沙地鑲了道邊。瀝青紙的碎片,塗成粉紅色的水泥,因為生鏽而發紅的呈波紋的屋頂,木板牆因為風化而閃著銀光,像補丁般綴滿壓扁了的裝煤油的錫罐,樁柱支撐的簡陋小屋,未燒完的煤渣皮殼在暗淡、低處的葉子上若隱若現。還有寥寥幾朵花。這是一月。但是成串的椰子樹依偎在棕櫚樹搖曳的樹枝下,高遠、纖小、柔和的雲朵,像春天裡由著自己的性子變幻不定的雲,在提醒這裡開花的季節和收獲的季節是平行的,永遠如此:發芽和結果不停地互相交織。眼前的景色中看不到任何山峰。小島很低,他們坐著飛機登上來時,它就像聖馬丁的一個平面雙胞胎或者說草圖,猶如一組佛蒙特的山峰,從大海中刺出來。海岸時而陡峭危險,時而又安全無虞。時而可以看到荷蘭人和法國人建的忙忙碌碌的旅店和飯館來,時而又發現陌生客人跡罕至。時而,感覺這裡連取地名都不當回事。如東角,西角,大路,森林——因此小島在地理上被分成好幾個部分。灌木叢和碎珊瑚石構成的荒蕪的山梁構成海灣的一側,被稱為高山。這個村子直接就叫海灣。海灣另一側橘黃色的懸崖索性就叫懸崖。在短暫的鼕日裡,太陽落在懸崖上方的對角線上,在六七點之間,又觸摸著大地最遙遠的手臂的指尖邊的大海。但是,當太陽沉沒後,本身已經變得慵懶的陽光,還在小木屋和夾竹桃的灌木中流連。現在是下午的晚些時候,小小的熱帶太陽還沒有漲成紅色,依然耐心地透過寂靜的空氣向下灑著白色的光芒。空氣柔軟如海水,雙方都沒有敵意。素,當拉爾夫從其中一個走出來進入另一個時,仿佛有那麼點獨立圍裹的受用色彩。
“噢,沒錯,但不僅僅如此,”醫生的妻子說,“他很喜歡這兒的人,給他們建了三個教堂,哦,而且還做了各種好事。我們正在說約翰遜牧師呢。”她對伊芙解釋說,她剛纔跟那幾個孩子在海灘上。“那位聖公會的牧師。去年退休了,然後就回英國了。我想是回蘇克塞斯了吧。”
“他愛這兒的人?”伊芙問道。她以前聽說過。話語聲在空氣中傳播得挺流暢,白天,隻有浪花輕吟的拍打聲和用英語喊叫偶爾傳來的人聲纔會干擾這樣的談話,那偶爾傳來的聲音因為調子隱約難辨,有那麼點樂感。
醫生的妻子蹲在沙地上。“這是我的幾個孩子,”她嘰嘰咕咕地說。她用尖利的笑聲驅走了突如其來的魯莽拙劣的模仿。“噢,沒錯,他愛他們。他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給了他們。”她的聲音中洋溢著青春的興奮,眼睛裡充滿天真的清澈,這一切都與她的身體顯得不搭調,因為她已經是中年的身材了。她肥胖的大腿已經顯得臃腫和虛軟,小臉上已經出現了細細的皺紋,每條皺紋都被一條白線所強化,那裡發皺的皮膚躲過了太陽的照曬。“他沒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她想補充一句。“隻有那條可怕的狗,鉤子。這個老人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也許會喜歡他。我相信你在美國從沒有見過這種人。”
“我知道,我們也會喜歡他。”伊芙說。“漢娜經常提起約翰遜牧師。”漢娜是他們的廚子,已經三十多歲了,可是還像個女孩子般羞怯和難為情。她的皮膚總是閃閃發光,好像總在不好意思,可是在廚房裡,她的樣子卻開心極了,經常自己哼哼贊美詩。孩子們起先有些害怕她的膚色,不過卻很服她,隻要她豎起一根兩種顏色的食指,告訴他們要學乖時,他們聽得眼睛都會開心地滴溜轉。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嚴肅地受過要學好的教誨。拉爾夫和伊芙沒有想過要找個用人。他們挑選了這個自己能找到的最默默無名的小島。不過漢娜是隨這房子來的,房東是個苗條細長的寡婦,孩子都在秘魯的佛羅裡達和安提瓜島,她覺得他們會需要她。結果還真需要。他們從來都沒有能力單獨解決這個新奇的世界的各種謎團。伊芙都沒法去買東西,因為難免要攙和些家長裡短——看不見的話語像風一般流動著,在講著誰家剛剛宰了頭豬,誰家的漁船滿載而歸。這個村子到處都是小鋪子;幾乎每家至少都出售——以煩人的差價——從聖馬丁走私過來的美國香煙。可是,那家最正規的鋪子,一個跟海關辦公室相連、由架子構成的水泥廊,即便在營業時間,在這家美國人看來,也是個難以敲開的謎團。他們總是看到那扇上了門閂的綠色大門,上面用粉筆寫著那句古老的告示:“各位注意了!各位朋友注意了!本店將在禮拜四關門。”
“噢,漢娜。是個不錯的姑娘,”醫生的妻子說,然後翻過身把腹部挨在地上。她那滿是皺褶的大腿背部霜一般沾滿了沙子,就像濕漉漉的砂糖。
“你知道,她是不錯,”伊芙說,“她很可愛。我覺得他們都很可愛。在我們看來,他們都挺可愛。”這樣的執著不像他妻子。拉爾夫有些納悶,這兩個女人到底怎麼了,她們一天前剛剛認識。“我明白約翰遜牧師為什麼喜歡這裡的人們。”伊芙用刻意但稍微克制的溫柔的語調補充道。“這裡的人們”全都在他們四周,他們的小木屋已經向下延伸到沙地邊緣了,而且窗戶緊閉,斑駁陸離的牆壁似乎在專注地聆聽著什麼。
醫生的妻子又翻過身來,恢復成某種坐姿。是什麼讓她這樣煩躁不安?
“沒錯,”她說,一波極其猛烈的浪花激起白色的斜坡,差點就要泡著她們的腳了。沙地裡全是泡沫孔。說不清的戳痕點綴其間,那是蟹的呼吸孔。醫生妻子的雙眼凝望著地平線,從側面看變成沒有顏色的透鏡。她鼻子的側翼顯得格外尖削。“他們都是些心地質樸的人。”她說。
醫生的妻子稱得上是這裡的皇後。她是住在這個小島上的唯一純粹的白種女人。當罕見的英國官員和更為罕見、小得難以置信的皇室成員惠顧這個及其遙遠又溫順聽話的小片帝國皇土時,她就是本地的女主人。每當她坐著自己那輛弄得泥土飛濺的英國福特牌小車沿著土路轟轟隆隆地駛過來時——車上的消音器早就腐爛掉了——那些上了年紀的土著就會揶揄地舉手加額,小孩子們則在尾隨其後的塵土中揮舞著胳膊。當她和醫生屈尊請求這家美國人在海灣住上三星期時,漢娜驕傲得渾身顫抖,都打碎了廚房的一隻杯子。醫生是個說話語速很快的小男人,透著股不得志的詼諧勁兒。因為經常抽走私香煙,他的指尖已經被熏成深黃色。他喜歡抽駱駝牌,不過目前隻有切斯特菲爾德香煙纔進得來。駱駝牌在他們當中還是多有摩擦。他從沒見過一根帶過濾嘴的煙。他和妻子在熱帶地區——英屬圭亞那、特立尼達島、巴巴多斯島住了十年,如今又住在這裡。他隱隱約約有過去美國的打算,賺上大筆錢,然後退休,生活在約克郡的一個村子裡。休假時他就去聖馬丁。
“如今,在美國,”醫生的妻子說,用膝蓋劇烈地蹭著沙子,“有色人群待遇好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伊芙問道。
“他們的運氣還好嗎?”
“還真不好,”拉爾夫說,因為他感覺由他而不是伊芙來回答要更好些。“有些地區好點,有些地區差些。當然,在南方,他們是公開遭到歧視的;在北方,他們很大程度上隻能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但至少還享有充分的法定權利。”
“噢,天吶,”醫生的妻子說,“這算是個問題,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