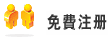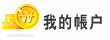第一章
一九一三年,從莫斯科乘車,經華沙轉車,前往查令十字,全程需花費十四英磅六先令三便士,以及兩天半的時間。一九一三年三月,弗蘭克·裡德的妻子內莉從赫莫夫尼基區的利普卡街二十二號出發,踏上了這趟旅程,還帶上了她的三個孩子——多莉、本和安努什卡。安努什卡(或安妮)兩歲九個月大,比起另兩個孩子,她有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煩。可是,那位在利普卡街二十二號照顧孩子們的保姆杜尼亞莎並未與他們同行。
杜尼亞莎肯定知情,弗蘭克·裡德卻蒙在鼓裡。從印刷廠回到家中後,他纔從一封信中首次聽聞此事。僕人托馬口告訴他,信是由一位信使送來的。
“他現在人在哪?”弗蘭克手中拿著信問道。信由內莉親筆所寫。
“他去忙別的事情去了。他歸信使協會管,協會不準他隨便休息。”
弗蘭克徑直走到房子右後方,接著走進廚房,發現那位信使正在那裡,同廚子和她的幫廚一起喝著茶,信使身前的那張桌上放著他那頂紅帽子。
“你是從哪裡拿到這封信的?”
“有人打電話叫我到這棟房子來,”信使一邊起身,一邊說道,“然後給了我這封信。”
“誰給你的?”
“您的妻子,葉連娜·卡爾洛夫娜·裡德。”
“這房子是我的,而且我就住在這兒。她怎麼還用得著信使呢?”
被稱為“小哥薩克”[ 哥薩克(Cossack)是一群生活在東歐大草原(烏克蘭、俄羅斯南部)的遊牧社群,是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內部具有獨特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地方性集團。——譯者注,下同]的擦鞋男僕,正在進行每周例行工作的洗衣女工,女僕,還有托馬,此時已悉數進入廚房。“他本該按吩咐把信送到您的辦公室,”托馬說,“可您比平常回來得早一些,他還沒來得及去找您,您就找上他了。”弗蘭克生在莫斯科,也長在這裡;他雖生性冷靜且含蓄,但也知道,有時自己仿佛置身舞臺,得把生活演給別人看。纔四點鐘,天卻已經黑了,可他還是在窗邊坐了下來,當著眾人的面打開了信。他記得,結婚這麼多年,自己頂多收到過內莉兩三封信。沒這個必要——兩人幾乎從不分開,況且內莉總是話很多。或許,最近說的沒那麼多了。
他盡可能放慢速度讀著信,可信上僅有寥寥幾行字,隻說她走了。回莫斯科的事隻字未提;他斷定,她不願告訴他問題到底出在哪,之所以做此論斷,主要是因為她在信的末尾說,她寫下這番話的時候絲毫不覺得痛苦,也希望他以同樣的心情接受這一切。信上還提到了“保重”之類的話。
眾人默默站在那裡看著他。弗蘭克不想讓他們失望,便小心將信折起來,放回信封裡。他看向窗外昏暗的院子,院裡堆著鼕天用的柴火,如今還剩最後一捆。鄰居家的油燈亮著,可以透過後院的籬笆看見零散的燈光。弗蘭克先前同莫斯科電力公司達成協議,在家中安裝了二十五瓦的照明設備。
“葉連娜·卡爾洛夫娜走了,”他說,“還帶走了三個孩子,至於她會走多久,我還不清楚。她沒告訴我她什麼時候回來。”
女人們哭了起來。她們肯定幫內莉打點過行李,並且得到了那些沒裝進旅行箱的鼕衣,但她們的眼淚與傷悲一樣,都貨真價實。
信使手裡拿著他的紅帽子,依然站在那裡。“給你錢了嗎?”弗蘭克問他。那人說還沒有。付給信使協會的錢在某個固定範圍內,從二十到四十戈比[ 戈比(kopek),俄羅斯等國的輔助貨幣;一百戈比等於一盧布。]不等,可問題在於,這位信使是否掙得了分毫。院子裡的雜務工此時進入廚房,也將煤油與鋸屑的味道,以及某種明顯的寒冷氣息帶進了屋內。早些時候,他肯定盡心盡力地幫內莉搬運了行李,雖然如此,可弗蘭克還是得把所有事情向他再解釋一遍。
“把茶端到客廳去。”弗蘭克說。他給了信使三十戈比。“我六點喫飯,和往常一樣。”一想到孩子們不在家,多莉和本不會放學回家,安努什卡不在屋子裡,他就有種窒息的感覺。三個孩子今早還在他身邊,可現在,他卻一個也不剩。眼下,他不知自己將來會有多麼想念內莉,也不知自己此刻有多想念她。他決定暫時不去想這件事,待以後再來評判此事對他有多大影響。他們之前一直在考慮去英格蘭一趟;弗蘭克惦記著這件事,早就去當地的警察局和中央警察機關為家人辦好了國際護照[ 在俄羅斯,人們有兩本護照,一本叫“國內護照”(internal passport),一本叫“國際護照”(external passport),前者相當於我國的身份證,後者相當於傳統意義的護照。]。也許內莉在護照上簽名的時候,腦子裡便有了種種想法。可內莉又是在何時允許這些想法進入她的腦子裡的呢?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弗蘭克的父親在莫斯科創辦了裡氏公司,那時,該公司做的是進口與裝配印刷機械的生意。作為副業,他還收購了一家規模較小的印刷廠。弗蘭克幾乎隻留下了那家印刷廠。如今,來自德國以及直接進口的競爭太過激烈,很難靠裝配廠掙到錢。不過裡德印刷廠生意足夠興隆,他還找到了一個通情達理、讓他感到滿意的人來做管理會計方面的工作。不過,說起塞爾溫,也許“通情達理”這個詞並不適合他。他沒有妻子,似乎從不抱怨,是托爾斯泰的追隨者,自從托爾斯泰去世後,他甚至更加堅定不移地追隨起托爾斯泰來;他還用俄語寫詩。弗蘭克以為俄國詩歌與樺樹和雪有關;事實上,在塞爾溫最近讀給他聽的幾首詩裡,樺樹和雪均曾被頻繁提及。
弗蘭克走到電話前,搖動兩次搖把,請求接通裡德印刷廠的電話,又反復請求了幾次。與此同時,托馬端著茶壺現身了,是個小號茶壺,想必很適合這位落了單的一家之主。壺裡的水馬上就要煮開,發出了微弱的嘶嘶聲,讓人有些期待。
“我們該拿孩子們的房間怎麼辦,先生?”托馬低聲問道。
“關上他們房間的門,讓房間保持原樣。杜尼亞莎在哪兒?”
弗蘭克知道,她現在肯定宛如一隻犁溝裡的山鶉,正躲在屋子裡的某處,以免被他責備。
“杜尼亞莎想和您談談。既然孩子們都走了,那她以後做些什麼呢?”
“告訴她,讓她盡管放心。”弗蘭克覺得自己說起話來就像是個任性的農奴主。想必他從未找過他們的大麻煩,讓他們擔心自己會丟掉飯碗吧?
電話接通了,塞爾溫用俄語說道:“我正聽著呢。”他的聲音很輕,似乎若有所思。
“聽我說,我今天下午本來不想打擾你,可出了些我沒料到的狀況。”
“你似乎有些不對勁,弗蘭克。跟我說說,你遇上什麼事情了,是高興事還是傷心事?”
“照我說,這事還挺讓我震驚。如果非要二選一,那我選‘傷心事’。”
托馬退出起居室,去門廳待了一會兒,說了些“將來會有一些變化”之類的話,然後退到廚房。弗蘭克繼續說道:“塞爾溫,這事跟內莉有關。我猜,她回英格蘭了,還帶走了孩子們。”
“三個都帶走了?”
“是的。”
“可是,她會不會是想去見一見·····”塞爾溫猶豫了一番,仿佛很難找到恰當的字眼來形容普通的人際關繫,“······難道有人不想見一見自己的母親嗎?”
“她一個字也沒說。再說,我還沒遇見她的時候,她母親就過世了。”
“那她父親呢?”
“隻有她哥哥還活著。他沒搬過家,一直住在諾伯裡。”
“弗蘭克,你居然娶了個諾伯裡的孤兒!”
“呃,照你這麼說,那我也算孤兒,而且你也算。”
“啊,可我都五十二了。”
塞爾溫腦子很好使,這股聰明勁兒常能派上用場,會在他工作時,也會在其他時候,在人們幾乎不抱希望的時候出人意料地顯現出來。他說:“先不說了。我正在對照出納實發的工資核對工資單。你說過,你希望能多做做這件事。”
“我確實希望能多做做這件事。”
“忙完這件事以後,要不和我一起喫飯吧,弗蘭克?我可不希望你就這麼干坐著,興許正······盯著一把空椅子看。去我家,簡單點兒喫,不去飯店,那裡的環境一點兒人情味兒都沒有。”
“謝謝你,不過還是算了。我明天早上去廠裡,跟平常一樣,大概八點到。”
他將聽筒放回堅固的銅制座架上,在屋裡巡邏起來,屋裡很安靜,隻聽得見從遠處的廚房傳來的此起彼伏的聲音,那聲音很耳熟,似從某場熱鬧的派對傳來,不過也能聽到某種別的聲音,仿佛突如其來的嗚咽聲。按照弗蘭克的標準,這棟房子有些搖搖欲墜,但很寬敞,房子的一樓是石砌的,二樓是木造的。巨大的爐子表面鋪著產自普列斯尼亞區的白色瓷磚,讓整個一樓都很暖和。屋外,朝著莫斯科河的河灣方向看去,隻見一道奇特的淺黃色亮光劃過了暗藍色的天空。
正門口處站著某個人,接著,托馬將塞爾溫·克蘭請進了屋內。盡管弗蘭克幾乎每日都會在印刷廠見他,可他常常會忘記,塞爾溫雖然是個英國商人,但看起來很不同尋常,直到他換了個環境見到塞爾溫,他纔想起這一點來。塞爾溫又高又瘦——就此而言,弗蘭克也一樣,可他還是個苦修者,笑起來很和善,探究起事情來很認真,看起來不太清醒,他似乎任憑自己日漸消瘦下去,一開始還顯得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後來幾乎變成了透明人。他身著一件黑色長大衣,穿著一條英式粗花呢長褲,長褲出自一位莫斯科的裁縫之手,做得短了一大截,他還穿了一件俄國農民常穿的高領工作服,以此來紀念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屋內很暖和,沒有女士在場,他便脫掉大衣,讓工作服粗糙的布料耷拉下來,堆疊在他瘦削的肋骨處。
“好哥們,我來了。聽到這樣的消息後,我可不能讓你自個兒待著。”
“可我寧願那樣。”弗蘭克說,“我要是明著說出來,你不會介意吧?我寧可自個兒待著。”
“我是坐二十四路有軌電車來的。”塞爾溫說,“我運氣挺好,幾乎一到車站就坐上了車。請放心,我不會待很久。辦公的時候,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我立馬便知道,這個想法興許能讓你好受一些。於是我立馬動身,朝外面的有軌電車車站走。弗蘭克,這種事在電話裡是講不清楚的。”
弗蘭克坐在對面,把頭埋進手裡。他覺得自己可以忍受任何事情,卻無法忍受別人執意以一種無私的態度待他。然而,塞爾溫似乎受到了鼓勵。
“懺悔的人纔會有這種態度,弗蘭克。沒必要這樣。我們都是罪人。我想到的倒是跟‘內疚’無關,而跟‘失去’有關,這也有個前提,那就是我們把‘失去’當作‘放棄財產’的一種形式。要知道,‘放棄財產’——或是世人用來表示‘放棄財產’的某種概念——不會讓人遺憾,隻會讓人欣喜。”
“不,塞爾溫,不是這麼回事。”弗蘭克說。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曾試圖把他所有的財產贈送給別人。”
“那麼做是為了讓農民更富裕,而不是讓他自己更貧窮。”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莊園離利普卡街隻有約一英裡遠。在遺囑中,托爾斯泰把這座莊園贈給了農民們,此後,那些農民便一直砍樹來換取現金。他們甚至在晚上也干活,借著煤油燈發出的光亮把樹砍倒。
塞爾溫身體前傾,一雙淺褐色的大眼睛異常專注地看著弗蘭克,眼中洋溢著好奇與好意。
“弗蘭克,到了夏天,我們一起去徒步旅行吧。我雖然很了解你,但若能在天氣晴朗的時候漫步在平原和森林裡,我應該可以更好地了解你。弗蘭克,你很勇敢,可我覺得你沒什麼想像力。”
“塞爾溫,今晚我可不希望有人來看透我的心思。老實說,我覺得我承受不來。”
托馬再次出現在門廳,幫助塞爾溫穿上了他那件散發著一股難聞味道的無袖山羊皮大衣。弗蘭克重申了一遍,他會在老時間到印刷廠。外面的門剛關上,托馬便失望地說,塞爾溫·奧西佩奇連一口茶也沒喝,甚至連一杯礦泉水都沒喝。
“他隻逗留了一會兒。”
“先生,他是個好人,總是在趕路,尋找著那些有需要或者絕望的人。”
“那他在這裡可找不到這兩種人。”弗蘭克說。
“也許他給先生您帶來了些消息,關於您妻子的消息。”
“要是他在火車站工作,興許他還真會給我帶來些消息,可他不在那兒工作。她坐上了去柏林的火車,我就知道這麼多。”
“上帝可不是毫無憐憫之心。”托馬含糊地說道。
“托馬,三年前,也就是安努什卡出生的那一年,你來到了這裡,那時候你曾對我說你是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托馬的臉松弛下來,露出了皮革般的皺紋,臉上寫滿了善意,看樣子,他已經準備好在接下來的數小時內進行一場漫無目的的討論。
“先生,我不是沒有宗教信仰,而是思想很自由。也許您從來沒有想過兩者的區別。要是我思想自由,我喜歡什麼,就能信仰什麼。今晚,鋻於您處境悲慘,哪怕明天一早我就不相信上帝存在,我照樣可以把您交給上帝,讓他來庇護您。要是我沒有宗教信仰,那我就有必要不去信仰任何宗教,這樣一來,我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可這是不合理的。”
過了一會兒,他們發現,塞爾溫的那隻公文包——實際上是個裡面塞滿了紙的樂譜盒,由於主人經常在有軌電車車站等車,等車的時候又多次淋雨,盒子已變得很僵硬——被留在了衣帽架下面的長凳上,衣帽架下面還放著成排的毛氈鞋。這種事之前曾屢次發生,熟悉的一幕倒是起到了某種安慰作用。
“明早我會帶著它去廠裡。”弗蘭克說,“記得提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