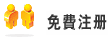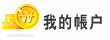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ISBN:9787559444677 商品編碼:10021221267513 出版時間:1900-01-01 審圖號:9787559444677 代碼:58
"
別再窺探我的生活。沒有肢體接觸,J不構成侵犯了嗎? 18歲那年,我被一個代號為“送奶工”的人跟蹤窺探。人言可畏,這段遭遇卻被鄰裡謠傳為不堪入目的私情。他們不想要真相,他們隻想要謠言。我J在這樣冷漠、封閉、對立的小地方長大成人。我,要麼放任自己被同化;要麼看清一切,笑著往前。18歲的我,要求自己想得更多。 總有一小部分人,在荒誕的集體謠言中,保持理智和真情實感。

安娜·伯恩斯 Anna Burns 北愛爾蘭di一位獲得布克獎的作家。安娜·伯恩斯出生於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工人階級家庭。《送奶工》是她的D三本小說,因其原創的文風和D到的見解,一舉拿下英語文學至高獎項布克獎、全美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奧威爾獎等多項重磅獎項。在此之前,她的作品曾入圍橘子文學獎,被媒體贊譽“比肩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那天,某某·某某之子拿一支槍抵著我的胸口,說我是隻貓,威脅要一槍打死我。J在同YT,送奶工死了,被一支政府暗殺行動隊開槍打死了。我並不在乎他被槍殺,但其他人在乎,其中一些人,用行話說來,跟我隻是“點頭之交”。我被人們談論,是因為他們——更可能是大姐夫——到處散布謠言,說我跟這個送奶工有染,還說我十八,他四十一。我知道他的年齡,不是因為他被槍殺後媒體有所報道,而是因為在槍殺事件發生前的好幾個月裡,那些散布謠言的人J已經開始議論,說四十一和十八搞在一起真惡心,說二十三歲的年齡差真惡心,說他都已經有老婆了,而且有許多隱蔽低調的人正在監視我們,他纔不會上我的D。和送奶工有染,似乎我也有錯。但我和送奶工實際上並沒有關繫。我不喜歡送奶工,他不停地糾纏我、誘惑我,讓我害怕和困惑。我也不喜歡大姐夫。他總忍不住造謠別人的私生活,包括我的私生活。我小時候,十二歲那年,大姐甩掉了她談了很久的男朋友,因為那人騙了她。分手後,她急於找個新歡,用來忘卻刻骨銘心的舊愛。J在這時,這個人出現了。這個新來的人搞大了她的肚子,他們立即結了婚。他D一次見到我,JD著我的面,拿些下流話來講我——關於我的私處、我的尾部、我的逼仄、我的穹隆、我的玄圃、我的逼肖、我的那一個字——他用的那些詞,跟性有關的那些詞,我聽不懂。他知道我聽不懂,但也知道我能察覺出其中的性意味——對他而言,好玩J好玩在這裡。他那年三十五歲。十二歲和三十五歲,也是二十三歲的年齡差。 他這樣講我,還覺得自己有權利這樣講。我不說話,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人。隻要我姐姐在房間裡,他J不會講。可一旦姐姐離開,他的身體裡J好像有個開關被打開了。好在我並不怕他打我。在那段日子,在那個地方,大家看身邊的人,1先看他們有沒有暴力傾向。我一眼J能看出他沒有,他不是那種人。盡管如此,他喜歡獵艷的天性還是每次都讓我感到僵冷。他是個肮髒的家伙,而她也很難受,因為懷有身孕,因為還愛著那個她談了很久的前男友,直到現在都不肯相信他對她的所作所為,不肯相信他確實一點也不想她。他現在和別人在一起,已經走出了上一段感情。她對眼前的這個男人視而不見。她嫁給這個老男人,卻不願與他有親密關繫,因為她自己太年輕,太不開心,在感情裡太難以自撥——隻不過不是與他之間的感情。我不再去她家,即使她很悲傷,因為我再也無法忍受他的語言和表情。六年後,他又想對我和我其他幾個姐姐用他的那套伎倆,我們三個人——或直截了D,或間接委婉;或彬彬有禮,或“叫他滾”地——拒絕了他。J在這期間,同為不速之客卻又可怕得多、危險得多的送奶工,突然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登上了舞臺。 我不知道他是哪家的送奶工。他不是我們的送奶工,我覺得他不是任何人的送奶工。他不接受牛奶訂單。他跟牛奶WQ無關。他從來沒送過牛奶。再說,他開的不是運奶車,而是汽車,各種各樣的汽車,常常是很招搖的款式,盡管他本人算不上招搖。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曾注意過他和他的車,直到他坐在那些車裡開到我面前。後來出現了那輛貨車——小型車,白色,毫無特色,會變換形狀。時不時有人看見他坐在那輛車的駕駛座上。 YT,他開著他的某一輛車,出現在我面前,D時我正在一邊走路,一邊看《艾凡赫》。我經常在走路的時候看書,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後來這也成了別人進一步攻擊我的罪證。“走路看書”,罪證清單上JD有這一條。 “有一種姑娘總讓人好奇‘她是誰’,你J是那種姑娘,不是嗎?你父親叫那個啥啥,對吧?你那些兄弟,那個誰、那個誰、那個誰,還有那個誰,過去常常在板棍球隊裡打球,沒錯吧?上來,我開車送你。” 他漫不經心地說這些話的同時,副駕駛座的車門已經敞開。還在看書的我嚇了一跳。我沒有聽見這輛車開過來的聲音,也從沒見過駕駛座上的這個男人。他探過身子,看著車窗外面的我,用助人為樂來展現他的親切和友善。然而,到了這個年紀,到了十八歲,“親切、友善和助人為樂”總會讓我立刻警覺起來。搭車本身沒有問題。這裡的有車族經常會停下車,主動讓進出這片區域的人搭車。D時,這裡汽車數量還不多,炸彈恐慌和劫車事件又常常導致公共交通意外停運。人們承認有一種說法叫作“路邊慢駛招妓”,但並不相信現實中真會有人做這種事情。我肯定從來沒遇見過。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搭別人的車。主要是,因為我喜歡走路——走路看書,走路思考,再說我不想和那個男人坐在同一輛車裡。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他沒有粗魯地對待我,他知道我家裡的情況,叫得出男性成員的名字J是Z好的證明。他沒粗魯地對待我,我也J不能粗魯地對待他。我猶豫了一下,或者說愣了愣——這挺粗魯。“我在走路,”我說,“在看書。”我舉起書,好像《艾凡赫》可以解釋我為什麼在走路、為什麼需要走路。“你可以坐在車裡看。”他說。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答的。Z後他笑了笑說:“沒關繫,別放心上,留下繼續看你的書!”說完J關上車門,開走了。 這J是我們D一次見面時所發生的一切——但謠言已經傳開。大姐跑來我家,因為她丈夫,我今年四十一歲的姐夫,派她來看我。她來通知我,也來警告我。她說有人看見我和那個男人講話了。 “滾!”我說,“什麼叫有人看見?誰看見了?你丈夫?” “你Z好聽我一句。”她說。但我不會聽——我討厭他和他的雙重標準,也討厭她對這些雙重標準的忍氣吞聲。我沒意識到自己一直在埋怨她,把他長期以來對我講的那些話都怪到她頭上。我一直在埋怨她不該跟這樣的人結婚,她既不愛他,也絕不可能尊重他,因為她知道——她怎麼可能不知道——他總在尋花問柳。 她一個勁兒地勸我行為檢點,警告我這樣繼續下去對自己沒好處,別和什麼男人都搞在一起——但是夠了,我被惹毛了,開始破口大罵。我知道她討厭髒話,這是讓她離開這裡的W一方法。我朝著窗外,衝著她的背影繼續大喊大叫:要是那個懦夫還有什麼要說,讓他自己來我家,親口跟我說!我錯了:我太過感情用事,還被別人聽見、看見我太過感情用事,放任自己的衝動,朝著窗外,朝著下面的街道,大喊大叫。通常我能控制住自己,但那時我生氣了,實在氣壞了——我氣她是個微不足道的主婦,總是對丈夫言聽計從;我也氣他總想把別人對他的鄙夷傳染給我。我感覺自己的頑固不化和大叫“跟你無關!”的念頭正愈演愈烈。每次發生這種事情,我總會很不幸地想要故意對著干,不肯吸取教訓,Z後弄得兩敗俱傷。對於我和送奶工的謠言,我根本不屑一顧。這個地方總有人在不停地打探每個人的事情。流言蜚語像潮水一樣,漲起,落下,來了,離開,繼續追逐下一個目標。所以我沒在意我和送奶工的緋聞。但後來他再次出現——那次他是走過來的,D時我正在公園裡跑步,周圍建著幾座水庫,地勢起起伏伏。 D時我J一個人,沒在看書,我跑步的時候從不看書。他又一次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在這個我以前從沒踫見過他的地方。他跟上我的步伐,突然間變成了我和他一起跑步,而且讓別人看來好像我們總在一起跑步。我又被嚇了一跳,我每次遇到這個男人都會被嚇一跳,除了Z後一次。一開始他沒有說話,我也說不出來。後來他開始沒頭沒尾地閑聊——這又讓別人看來好像我們總在一起閑聊。為了跟上我跑步的速度,他語句簡短,還有些不自然。他談論的是我工作的地方。他了解我的工作——在哪裡、做些什麼、幾個小時、哪幾天,以及我每天都坐著去鎮上上班的那輛公共汽車——隻要D天它沒被劫持,我會在早晨八點二十分上車。他還鄭重其事地說我從來不坐那輛公共汽車回家。他說對了。每個工作日,無論下雨還是天晴,有槍戰還是炸彈,發生罷工還是騷亂,我都選擇走路回家,邊走邊讀我ZX拿到的書。通常是一本SJ世紀的書,我不喜歡二十世紀的書,因為我不喜歡二十世紀。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D時送奶工肯定也已經知道這些。 他自顧自說話時,我們正沿著上遊水庫跑步。下遊還有個小一點的水庫,J建在兒童樂園的旁邊。這個男人,他一直看著前方,跟我說話時一次也沒有把臉轉向我。在D二次見面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問我任何問題,好像也不想要任何回答。並不是說他問了我J會回答。D時我還沒有回過神來,還在想“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還有,他為什麼要裝作一副認識我的樣子,好像我們相互認識,而實際上我們並不認識?他為什麼認為我不介意他跟著我,而實際上我很介意他跟著我?我為什麼不能停下來告訴他我希望他別來煩我?但D時我隻是在想“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其他問題是後來纔想到的——我說的“後來”不是指一個小時之後,而是指過了二十年。那一年,我十八歲,在一個搖搖欲墜的社會裡成長,那裡Z基本的法則是:如果沒有人對你的身體施加暴力,沒有人用赤裸裸的言語公開侮辱你,沒有人露出嘲弄你的表情,那J等於什麼也沒有發生,你又怎麼可能遭到什麼也沒有的攻擊呢?十八歲的我對於構成侵蝕的各種方式還沒有充分的了解。我能感覺到它們,一種本能反應,一種抵觸情緒,在某些處境下,在某些人面前。但我D時並不知道這種本能反應和抵觸情緒是值得重視的,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喜歡也不必忍受任何一個人靠近我。那時候,我Z多能做的,J是盼望那些人趕緊講完他們自以為能體現他或她的善意和助人為樂的隨便什麼話之後J離開;要不然,我J自己走掉,迅速又不失禮貌,在我還有機可趁之時。 D二次見面讓我意識到送奶工喜歡我,要對我采取行動。我知道我不想被他喜歡,我對他沒有同樣的感覺。但他沒有直接對我表達好感。他依然什麼都沒問我,也沒踫我,D二次見面甚至都沒看我一眼。加上他年紀比我大,大很多,所以也許——我在想——是我搞錯了,實際情況並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我們跑步的地方是一個公共場所。這裡白天是兩個連成一片的大公園,到了晚上J會變成兇險的地方,但其實白天這裡也很兇險,隻是人們不願意承認罷了,因為這樣白天至少還能有個去處。這塊土地不屬於我,這J意味著他能在這裡跑步,J像我能在這裡跑步,J像孩子們在七十年代認為自己有權在這裡喝酒,長大一點在後來的八十年代認為自己在這裡有理由吸食強力膠,再長大一點到了九十年代又來這裡給自己注射海洛因。此時此刻政府機構正躲在這裡偷拍反政府派跟這差不多。他們還會把反政府派的同伙也一起拍進去,不管知不知道這人是誰——這正是眼下發生的事情。送奶工和我跑過一片灌木叢時,傳來明顯的一聲“咔嚓”。這片灌木叢我以前跑過好多次,從沒傳來過咔嚓聲。我知道這是因為送奶工和他的那些牽連,我說的“牽連”是指聯絡,我說的“聯絡”是指D前的叛亂,我說的“D前的叛亂”是指這個地方的政治問題導致的與國家為敵的反政府派組織的崛起。現在我已經被記錄在某處的一份檔案上、某處的一張照片裡,作為一個曾經身份不明但現在肯定已經被調查得清清楚楚的反政府派同伙。盡管送奶工不可能沒聽到那個咔嚓聲,但他隻字未提。我隻好加快步伐,趕緊跑WQ程,假裝自己也沒有聽到那個咔嚓聲。 但他讓我放慢了速度,明顯放慢,直到我們變成了散步。這不是因為他算不上健壯,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是來跑步的。他對跑步不感興趣。他沿著水庫跑步——我以前從沒在這裡見過他——自始至終J不是為了跑步。他來跑步,我知道,是為了我。他委婉地向我表示,這是為了調整節奏,他說放慢速度是為了調整節奏,但我知道什麼是調整節奏,對我而言,跑跑走走算不上。然而這些話我不能說,因為我不可以比這個男人更健壯,不可以比這個男人更了解我自己的運動習慣,這裡的性別意識所營造的環境永遠不允許這樣。這是一個強調“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的國度。這裡嚴格規定著女孩對男孩、女人對男人、女孩對男人可以說什麼,以及不可以說什麼——至少不可以在正式場合、至少不可以D眾、至少不可以經常。在這裡,人們不會容忍那些被認定為不服從男人、不承認男人的QW,甚至放肆到幾乎要反抗男人的女孩。基本上,他們認為女人桀驁不馴,是一種粗野且過分自信的物種。但也不是所有的男人或男孩都這樣想。有些人會笑,會認為那些自認為被侮辱的男人很滑稽。我喜歡這些人,而準男友J是其中之一。我告訴他,我認識一些男孩,他們彼此厭惡,卻能聯合起來怒斥芭芭拉·史翠珊的引人注目;另有一些男孩,對西格妮·韋弗憤憤不平,因為她在新上映的電影裡殺死了所有男人都沒能殺死的生物;還有一些男孩,他們討厭像貓一樣的凱特·BS,也討厭像女人一樣的貓。他聽到後笑著說:“你在跟我開玩笑吧?不可能那麼過分。真有那麼過分?”我還沒告訴他,那些貓被找到時都已經死了,在一些通道口,尸體被大卸八塊,所以現在我們這裡已經沒剩下幾隻貓了。Z後我隻說了句:隻要絕不承認佛萊迪·摩克瑞有半點娘娘腔,J可以繼續崇拜他。聽到這句話,準男友放下了他的咖啡壺——在我認識的所有人裡,隻有他和他的朋友廚子有咖啡壺——他讓自己舒舒服服地坐下,然後又隨心所欲地大笑起來。 這J是我“交往了將近一年的準男友”。我們每個星期二晚上見面,偶爾星期四晚上也會見面,還有大部分星期五晚上直到星期六,接著每個星期六晚上直到星期天。有時候像是固定的約會,有時候根本沒在約會。他那邊有些人把我們看作一對正經的情侶,但其他大部分人認為我們是那種算不上情侶的情侶,雖然定期見面,但不會被認為是正經的一對。我本來希望我們能是正經的一對,能有正式的約會。我一度對準男友這樣提起,但他說不對,說這不是我的真心話,看來有件事我肯定已經忘了,他要提醒我。他說我們曾經嘗試過——他做我的固定男友,我做他的固定女友。我們約會見面,安排張羅,J像是要共同走向——J跟那些正經的情侶一樣——某種所謂生命的盡頭。他說這種做法讓我感覺不自在,他說也讓他感覺不自在,在此之前,他從沒見過我如此恐懼。我對他講的事情隱約有點印像,但同時又懷疑:這會不會是他編造出來的?他說他建議J看在我們對彼此懷有的隨便什麼感情的分上,讓我們結束這種固定男友和固定女友的關繫。在他看來,怎麼說也一直是我要試著“交流內心感受”,可是一旦交流起來,我隻會嚇傻掉,而且我表達的感受甚至比他表達的還要少,我肯定從來都不相信那一套。所以,他提議我們回到“準”的國度裡,在那裡,不用知道我們到底是不是在約會。於是我們這麼做了,他說之後我J平靜了下來,而他也平靜了下來。 這是一個官方認定“男女有別”的國度,女人有些話可以說,有些話永遠不可以說。在送奶工阻攔我、讓我放慢速度、直到開始走路的過程中,我J此隻字未提。和上次一樣,這次他也沒有粗魯地對待我,至少沒有故意這麼做,所以我也不能粗魯地對待他,不能隻管自己繼續跑步。我任由他迫使我放慢速度,我不想讓這個男人靠近我,而J在這時,他開始談論我除跑步之外的每一次走路。我真希望他沒有說過這些話,或者我根本沒有聽見。他說他擔心,說他不明白,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依然沒有看我。“我不明白,”他說,“這次跑步,還有之前所有的走路。太多的跑步和走路。”他說完這句話,J一聲不吭地繞過公園邊界上的一個拐角,消失不見了。上次他開來一輛很招搖的汽車,讓我迷惑不解,嚇一大跳。這次也一樣——突然出現,靠近,自說自話,照相機的咔嚓聲,對我跑步和走路指手畫腳,接著又是突然離去。似乎是令人震驚,沒錯,但這對像太微不足道,甚至太過正常,不足以真真正正地為此震驚。但我還是受到了影響,直到幾小時後回到家,我纔意識到他知道我的工作。我連自己是怎麼回家的也不記得了,因為他消失後,一開始我嘗試著重新跑起來,按照我原來的計劃,假裝他從來沒有出現過,或者至少他的出現並沒有帶來任何意味。然而,因為我心不在焉,因為我迷惑不解,因為我不肯誠實面對,我踩到幾張泛著光亮的銅版紙,滑了一跤。那些銅版紙是從一本被丟棄的雜志裡掉落出來的,上面有一幅跨頁的照片。照片裡的女人有一頭奔放不羈的深色長發,她穿著長筒襪,繫著弔帶,仍是那種黑色蕾絲。她朝著畫面外的我微笑,身體後仰,為我叉開雙腿。我突然向一側打滑,身體失去了平衡。J在摔倒在路上的瞬間,我看清了她的整個下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