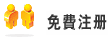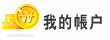三“新東北作家群”的未來
如同現代文學史上的傳奇復現:一群來自東北的青年作家,以他們的寫作震動文壇。對於逐漸邊緣化的當代文學,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們,文學不是一種可以分離出去的“專業”,而是從來都和生活血肉相連。但是當他們站立在文壇的中央,未來何去何從?八十年前的傳奇,並沒有圓滿的收場。
在“新東北作家群”中,班宇對未來有一個戲謔而不乏深刻的展望:
2035年,80後東北作家群體將成為我國文學批評界的重要研究對像,相關學者教授層出不窮,成績斐然。與此同時,瀋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文學之都,東北振興,從文學開始。
2065年,文學將進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戶,即可下一單文學作品,以供閱讀。可對語言、流派、字數、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種項目進行勾選和填寫。宣傳口號或為:××外賣,寫啥都快。生命科學技術取得長足進步,博爾赫斯於同年復活,醒來的第一句話是:天堂不是圖書館的模樣,地獄纔是,感謝你們將我拯救出來。次月,他覺得仍處地獄,不曾脫離。
2095年,文學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已不存在,無人提起。隻有一少部分人進行秘密結社,堅持從事寫作這種古老活動,被視為正統社會的異端,生存空間極其狹隘。他們試圖與寫作機器對抗,但屢屢挫敗。同年某地下室,東北作家群體遭逢博爾赫斯,並將其擊倒在地。原因不明。q
班宇這段“展望”觸及了宰制“新東北作家群”的多重維度:學術體制、純文學、技術現代性社會。他們的寫作首先被學術體制化,之後面臨著演進到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化文學的壓制,被“寫作機器”及其對應的非人化的技術現代性社會所取消。而這一切的結局—或者說開始—是作為像征的博爾赫斯。在一個文學黑客帝國般的世界裡,從事地下抵抗運動的“新東北作家群”遭遇博爾赫斯並將其擊倒,不知道他們在百年後能否逆轉未來?
技術現代性社會將毀滅文學,而將文學知識化的文學批評與將文學技術化的純文學寫作,構成了技術現代性社會的文學建制。由此反推,“新東北作家群”寫作的未來,在於能否抵抗技術現代性社會及其文學建制。“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作為當代文學的岔路口,使得兩條道路得以顯豁:一條道路是“文學是數學”,就像《黑客帝國》中的尼奧被史密斯感染,“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將變得技術化,文學和當代世界數字化、金融化、符號化、虛擬化的邏輯契合,脫實向虛,成為一種技術化的敘述遊戲,直至被取消;一條道路是“文學是人學”,“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從東北開始,重構文學與生活的聯繫,在歷史的連續性中展開敘述,保衛真實的情感與人性。
“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勢必將挪動兩個文化政治坐標:技術現代性社會中“東北想像”的位置、文學場中“東北文學”的位置。有以下諸種的主流“東北想像”彼此交疊:基於市場經濟視點,“東北”被視為官僚化的計劃經濟殘留;基於現代化邏輯的視點,“東北”被視為貧困的欠發達地區;基於都市文明視點,“東北”被視為愚昧的鄉村;基於現代理性社會的視點,“東北”被視為粗野的奇觀。總之,“東北”被視為以理性、技術、效率為內核的現代性文明的“外部”,這種現代性想像在當下處於絕對的霸權地位。
基於這種霸權想像對於“東北文學”的限定,一方面“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受到文壇歡迎,東北文學的冷峻殘酷,有一種奇異的魅力,填充以往小資化寫作的貧乏虛無;另一方面,“東北文學”被理解為一種地方文學風格,“新東北作家群”的作家們被無意識地暗示要走出“東北”,變成“成熟”的職業作家。
“新東北作家群”承受壓力的地方正在於此。落實到寫作上來,成名後的雙雪濤、班宇等開始表露出求新求變的傾向。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作家》上發表《山脈》,小說共分五節,炫技般地先後使用文學評論、訃告、日記、小說、創作談五種文類,彼此互相指涉,構成敘述的迷網。其中第四節即小說段落是我們熟悉的班宇小說,塑造了一個善良、懦弱、愛讀書的在持續的侮辱中失蹤了的工人。然而這樣一個故事陷落在前前後後的敘述網絡裡,共情被懸置,意義指向變得陌生化。班宇在此對於自身“寫作”(小說中“小說家班宇”出場)刻意暴露、中斷、戲仿,試圖在尋求一種新的寫作方法。同時,班宇在《喚醒疲憊之夢》這篇文論中反思“小人物”書寫:
對於“小人物”的書寫,在今日而言,與其說是慣性,不如看作是一個傳統而安穩的起點,一種陳腐、倉促但卻可以身體力行的抵抗手段,每個人似乎都可以從這裡開始,貢獻或者嘔吐出自己的經驗,並將其作為批判與抗議的工具。與此同時,所有的敘述又都很難不淪入上述的想像境況—寫作者不再與自身的固見作鬥爭,也沒有經過破裂與自我組建,隻是站在高臺上展示出來,成為大大方方的輸家,扯開一面旗幟,落寞與潰敗在此迎風招展。在這樣的困境裡,書寫的突圍變得難以實現。r
筆者以為,班宇《逍遙遊》等小說已經為“寫小人物”創制了一種新的敘述,但這種文學實踐還缺乏足夠的討論,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猶疑。和班宇的反思相比,雙雪濤走得更遠。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2018年11月23日)中,雙雪濤談到:
說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為烏有》,我覺得這兩部小說寫得有點問題,這兩部小說寫得有點機巧,尤其是《北方化為烏有》。這個題目雖然比較容易被人記住,但我稍微有點武斷。我可以辯解說“北方”是見聞,或者我永遠不承認“北方”是瀋陽,但這明顯帶有一點狡辯的意味。根據小說敘述的設計,在一個集中的環境、準確的時間—除夕夜,人物往我視域上靠攏,寫得比較集中。現在看這個小說寫得還是緊了一點。出發點其實是敘述的樂趣,而不是追求歷史真相,但寫著寫著就自動把你帶到那個東西裡面去了,去尋找當時真實發生了什麼。s
在雙雪濤2019年結集出版的小說集《獵人》中,東北的場景與故事基本上化為烏有,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編輯、出版人、編劇、導演、制片人、演員、明星、經紀人、記者等人物。唯一的東北故事是《楊廣義》這一篇,作為“神刀楊廣義”,這個1990年代的工人依賴傳說中的刀法,逃逸在傳奇之中。理解《獵人》和雙雪濤的變化,代表性的作品是《武術家》,從“九·一八”之後的奉天寫到“文革”期間的北京,國仇家恨不過是日本武士邪術作怪。小說結尾,主人公借助一句咒語“春雨細蒙蒙 我身近幻影”,將日本武士的“影人”化為一縷飛煙。
小說貌似荒誕不經,實則作者有深意存焉。貫穿《武術家》始終的,是對於“身”與“影”也即“實”與“空”的辯證討論,小說也是在這一哲思下,刻意以“輕”寫“重”。但通讀下來,實在難言成功。這篇小說以過於輕易的敘述解構20世紀的諸種“大敘事”,小說隻是借助詞語的魔法來完成復仇,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敘述的樂趣”的旨趣所在。假設以這種敘述策略重寫《平原上的摩西》,將1990年代的工人一代講述為不過是中了日本武士的邪術,困在9學費前的少年們是看不清“我身近幻影”,不知道能否說服曾經的
作者?
雙雪濤的文學世界中一直有一條奇幻書寫的暗線。他寫過一篇致敬王小波的《我的師承》t,王小波無疑是敘述的大師,但學習王小波很容易流於表面。王小波的敘述天馬行空,奇趣橫生,但敘述深處有不可化約的沉痛。王小波由創傷、記憶討論到革命、技術現代性,始終聚焦在20世紀現代性的核心議題與當代中國歷史實踐的交錯。把握不住王小波敘述背後的思想性,很容易流於敘述的遊戲,
述指向的是一種虛無的逃避。有論者將王小波小說視為“犬儒主義哲學”u,固然有些簡單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說,但也點中了王小波流行開來的時代氛圍。
雙雪濤的小說結尾常常以“湖”“河”“大海”或“天空”結束,有論者指出雙雪濤以“水”結尾,是對歷史性的失序之後墜落的恐懼,“水”是作者恐懼感的物質賦形v。這種看法有其道理。筆者就此補充的是,無論是陷落在水中還是消失在空中,是將無法解決的現實矛盾想像性地解決,如雙雪濤在《天吾後記》(臺灣版,2019年出版)序言中所言,觀察生活和書寫生活可能是逃離生活的辦法。雙雪濤東北書寫中的“傳奇感”,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出生於1983年的雙雪濤與郭敬明等“80後”作家盡管出道前後差了十多年,但他們是同齡人,郭敬明的《幻城》《爵跡》以及網絡文學中的玄幻文學,長久地居於青春文學消費市場的主流。規訓郭敬明以及網絡玄幻作家的文學生產機制,對於雙雪濤而言,同樣構成了塞壬的歌聲。而雙雪濤對於奇幻故事並不陌生,無論是長篇處女作《翅國》還是被改編為電影的短篇小說《刺殺小說家》,他的奇幻書寫雖然遠遠不如東北書寫,但一直綿延不斷,在《獵人》中重新翻為主流。
雙雪濤的奇幻寫作也不乏出色作品,《獵人》中的一篇是《火星》。一對中學戀人多年以後相見,一個窮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被極為精彩地翻轉,語言節制準確,布局謀篇老練,敘述上極為成熟。然而這篇小說骨子裡是鬼怪加情義的都市傳奇,小說像征性地發生在“上海—山區”,面對著尋求刺激與慰藉的中產階級受眾。因雙雪濤目前所在的文學場的位置,一個定居在北京的職業作家,一個面向都市受眾的電影編劇,“都市傳奇”有可能取代“東北往事”成為他主要的文學方向。
筆者在2017年化用文學史經典概念,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呼告“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這一提法屢遭善意的譏諷。隨著班宇、鄭執等一批作家的崛起,筆者當年的預判沒有落空。但這裡筆者不是為預見實現而自鳴得意,相反,當時的憂慮在今天可能更為迫近。雙雪濤當下的寫作,處於一種歷史性的分裂之中,就像《火星》中的主人公一樣:不斷地自我暗示,“必須承認自己,自己,自,己,是僅有的東西”w;同時和這種奮鬥口號般的暗示永遠糾纏在一起的,是不斷浮現的遠方和青春歲月的回憶。
在一個集體的意義上,“新東北作家群”更大的困境,是怎麼處理“階級”與“地方”這兩個範疇的往復辯證,這兩個概念長久以來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一批書寫“下崗”的作家被窄化為“地方”作家,在這個意義上,包括筆者提出的“新東北作家群”等等既是一種便捷的命名,也是一種必須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從“尋根文學”以來的文學範式中掙脫出來,解構“地方”這個範疇的束縛,書寫超越地方的總體現實以及對應的情感結構?沒有這一文學範式的轉移,無法實現普遍化的共情,無法打破地方與地方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堅冰。必須點題,“新東北作家群”不是指一群東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現代主義文學資源的“新現實主義作家群”。在這個意義上,“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將不僅僅是“東北文學”的變化,而是從東北開始的文學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