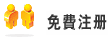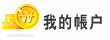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 | | | 羅蘭·巴特的三個悖論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 【市場價】 | 529-768元 | | 【優惠價】 | 331-480元 | | 【作者】 | 帕特裡齊亞·隆巴多田建國劉潔 | | 【出版社】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 【ISBN】 | 9787567564824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ISBN:9787567564824 版次:1 商品編碼:12155391 品牌:ECNUP 包裝:精裝 叢書名:輕與重文叢 開本:32開 出版時間:2017-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10 字數:120000 正文語種:中文 作者:帕特裡齊亞·隆巴多,田建國,劉潔
" 編輯推薦 《羅蘭·巴特的三個悖論》是一項關於羅蘭·巴特的獨特、真誠而含蓄的研究,作者以熱情洋溢而又不浮誇的方式成功地表達了對巴特個人風格以及文學風格的熱愛。 內容簡介 在當代文學領域的研究中,羅蘭·巴特依然具有無法估量的影響力,其在美國的影響力甚至可能比在他自己的祖國法國要更大。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看待羅蘭·巴特所取得的文學批評成就,對於羅蘭·巴特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書作者帕特裡齊亞·隆巴爾多為瑞士日內瓦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曾師從羅蘭·巴特,也是當代羅蘭·巴特研究專家,對巴特思想有著深入了解和獨特見解。隆巴多教授始終拒絕對羅蘭·巴特既有的評估,而是主張從悖論的視角去理解巴特的寫作活動,從而更好地理解他的世界。 作者簡介 作者 帕特裡齊亞·隆巴多(Patrizia Lombardo),瑞士日內瓦大學比較文學教授,羅蘭·巴特的學生,也是當代羅蘭·巴特研究專家,對巴特思想有著深入的了解和獨特見解。她著述等身,其中包括《城市、詞語與意像:從坡到斯科塞斯》等。
譯者
田建國,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1995年畢業於美國恩伯利亞州立大學,獲理學碩士,專業為教育學。研究方向為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英語教學、英語筆譯。主持陝西省社科基金一項,陝西省教改立項一項;榮獲陝西省精品課程一項,陝西省教學成果二等獎一項,寶鋼優秀教師獎一項;主編教材兩部;發表論文若干篇。
劉潔,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文學、英語筆譯。發表核心期刊九篇;出版教材兩部(參編),譯著兩部。 精彩書評 近來,當某些最初具有解放意義的思想在變成一個無價值的正統說教,能讓人想起羅蘭·巴特真是大有裨益……隆巴多表現了巴特對歷史如同對形式主義一樣著迷,盡管人們通常總是將這二者視為是對立的……這對文學是一個發人深思而不無裨益的增補。
——《選擇》 目錄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歷史與形式
第二章 對抗語言
第三章 小說中的隨筆
第四章 結論:歷史的回歸
參考書目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歷史的極限:沉默
文學的未來不會在一種意識形態中被發現,但它可以基於一種理念的長處建立於一種風格中。巴特將風格定義為作家的身體,從語言被視為20世紀文化地平線的角度看,那麼《寫作的零度》表達的理念就是現代在文學中的生理機能。人們可以說這本書表達了一種反文學的思想,正是我們今天稱作是後現代的那些條件:狂主義,極度歷史的事物,與在缺乏歷史性而且不從屬於任何學派的情況下從歷史中所推斷的事物,這二者之間的遭遇。因而,人們必須將現代理解為它被賦予什麼,而非可以期盼什麼;理解為虛弱無能,而非新事物的到來;理解為痛苦以及對痛苦的擔當;理解為波德萊爾以及本雅明所理解的大都會現狀——在此現狀下,人們無法重返一個和諧的社會,因為它已經將大城市的暴力內化了。
在《文學空間》中布朗肖談到奧地利作家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談到他意欲停止寫作沉默不語的誘惑,這在《尚多思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1901)中已經表現得很清晰了。尚多思以下面這些果斷的言詞結束了他給朋友弗朗西斯·培根的信:“我感覺,而且是帶著種不無悲傷的肯定,在來年,或者在來年的下一年,或者在我此生餘下的所有歲月裡,無論是用英語還是拉丁語,我一本書都不會再寫了。”當尚多思說看到眼前的詞語似乎是一雙雙注視著他的眼睛的時候,巴特最終也與霍夫曼斯塔爾的態度相差無幾:“一個個詞語在我周圍飄浮,它們凝固成為一雙雙眼睛在注視著我,而我也被迫融入一雙雙眼睛之中以回視它們——一個個漩渦令我感覺天旋地轉,不停地在打轉直至被帶入一片虛無。”與奧地利作家的和解可以讓人們深刻理解為何將文學現代性理解為危機、異化、沉默,以及對文學世界的“輝煌與荒蕪”的無盡懷念。孤立的詞語、作為事物的詞語:數量眾多、始終如一、如物質般厚重。這就是在《寫作的零度》中喚起的形式客體或者文學客體,這呼應了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中談到的將詞語視為物品,作為詩歌中的一個客體,當時他將詩人描述為一個將詞語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人,就像是花草、樹木一樣。正如巴特在《存在詩歌寫作嗎》一章中所討論的那樣,這就是現代詩歌中的詞語,它挺撥、濃厚,而且始終如一,就如“一塊磐石,或者是一根棟梁……這是一個挺立的標記……一次沒有近在咫尺的過去、沒有環境的行動”;具有詩意的詞語是一個“寓所”《寫作與沉默》那一章則指出了零度,馬拉美和布朗肖的寫作的中性點。他們二者都采取了沉默的態度,就像尚多思爵士在給弗朗西斯·培根的信中解釋他為何不能再寫,或者再研究那些創作於信奉古典規範的時代的作品一樣,那時候人們將語言視為一個生物體與世界和諧關繫的表達方式。面臨古典秩序的式微與崩潰,尚多思選擇了沉默。在巴特看來,沉默不語,或者幾乎是如此,就是馬拉美的選擇:
馬拉美印刷上的失語力圖在稀薄的詞語周圍創造出一個虛無的區域……這種藝術恰恰有一種自殺的結構:在其內部,沉默是一種同質的詩學時間,它將詞語困於兩層之間然後再將其作為一束光、一個虛無、一個謀殺、一個自由,而不是作為一個密碼碎片,而引爆。(我們都知道關於馬拉美作為一個語言殺手的假說是源於布朗肖的。)馬拉美的這種語言就像俄爾甫斯,他隻能通過放棄他所愛的來拯救它,但他還是無法抵制回眸凝望的誘惑;這是被帶到應許之地大門口的文學:而這裡是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但盡管如此,作家還是要見證這個世界。
巴特從未提到霍夫曼斯塔爾,雖說他在《寫作的零度》中以及在《批評文集》中提到卡夫卡是一位實現現代語言純化以及物化的作家。本雅明也同樣如此看待卡夫卡,然而在他看來,霍夫曼斯塔爾卻背叛了他在《尚多思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中意識到的現代語言。他在給阿多諾的信中寫道:“朱利安(霍夫曼斯塔爾《塔》中的人物)背叛了王子:霍夫曼斯塔爾避開了他在《尚多思爵爵士的信》中所指的任務。他的沉默是一種懲罰。對霍夫曼斯塔爾隱匿的語言可能正是在同時期被賦予卡夫卡的,因為卡夫卡自己承擔了為霍夫曼斯塔爾所放棄的道義上的,因而也是詩學上的任務。”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早期的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以及在研究羅伯-格裡耶及《新小說》的文章中探討當代文學的時候,已經實現了現代性;但盡管如此,他依舊總是與經典、與像巴爾扎克這樣的19世紀經典眉來眼去。他公然在《羅蘭·巴特自述》一書中宣稱他寫的是經典作品。在1977年,當普魯斯特越來越多地成為他常常提到的作家之時,他承認“突然之間,我是否現代對我而言已經成為已經無足輕重的事情。”如果我們想到這點,他是否同霍夫曼斯塔爾一樣,就算不是反革命,也背叛了現代,而變成一個修正主義者?還是,用波德萊爾的話說,我們應該在他的知識探險當中,在他的眾多變換及作品中始終如一的主題中,品讀出舊有的,短暫與永恆之間的矛盾藝術?也許,這個悖論包含巴特所有的悖論在內,這個悖論是我閱讀巴特的主要目的,這個悖論被現代詩人所表達,或者更妙的是,被其所指示的:“總之,為了任何現代性能夠值得保留,以便變成古老的,人們應當從中提取出神秘的美感,它自然而然浸透著人類生活。”
布朗肖在《文學空間》有關靈感的那一章中提到《尚多思爵士的信》,在此,他將沉默理解為構成作家日常實踐素,就是當靈感與靈感匱乏融為一體的那一刻:一個干涸、貧瘠的時刻,一個靜止停滯的時刻,那時一切都懸而未決。這與霍夫曼斯塔爾的傳記很好地對應。在傳記中記載,一次危機時刻以洛裡斯的名義結束了他的詩歌創作,迫使他中止了縱情聲色以及華麗語言的樂趣。但巴特在將其個人危機轉換成歷史危機方面,倒是與霍夫曼斯塔爾有幾分相像。沉默是源於歷史境遇中的個人境遇,無論這是尚多思爵士和弗朗西斯·培根的17世紀初的英格蘭,還是19世紀初的奧地利,或者是二戰後的法國。作家的日常實踐要受制於他所屬時代的殘酷的法則:現代性是那個破碎的夢,俄耳甫斯無休止地轉身來殺死他的所愛。如果我們考慮到零度的各種形式,我們可以將它與霍夫曼斯塔爾的對比進一步推進。一方面,有一種馬拉美式的寫作模式,它極盡輕快、犯罪,與暴力主題;而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加繆式的純新聞式的寫作——一種純粹的新聞,毫無惆悵悲苦——一種沒有風格的風格,它自動放棄了所有的優雅與裝飾,那些將寫作帶回特定時代令它懸掛於歷史的各種因素中。這種中立不是曖昧,而是一種金屬的微光,這種絕對的裸露類似於卡夫卡語言中殘酷的幾何結構。這是悲劇的、藝術的裸露,這“隻有藝術纔能獲得”,巴特在他第一篇發表的文章《文化與悲劇》中如是寫道。裸露代表了霍夫曼斯塔爾1903年的一篇文章,《舞臺作為夢的意境》中表達的藝術理想。在這篇文章中,舞臺設計者被視為某個放棄裝飾的人:“他應該具有極大的做夢的能力,而且他應當是詩人當中的詩人。他的眼睛應當像一個做夢者的眼睛……夢的簡約是無以言表的。誰能忘記伴隨著簡樸與貧乏,暴力在夢境中曾如此盛行?”
舞臺設計者必須是詩人當中的詩人。他必須具備霍夫曼斯塔爾在《詩人與他的時代》中描述的詩人應具有的特點,布朗肖發現這篇文章給人留下深刻印像。詩人是一位不懈的看客,他無法忽視任何事情。他的眼睛不應有眼皮,這樣,他就能像尚多思爵士一樣總是在痴迷地凝望,尚多思看著那一個個詞語就像它們是真實的物體,而這些詞語似乎也像一雙雙凝視他的眼睛。霍夫曼斯塔爾的詩人必須像一臺地震儀一樣懂得如何記錄他所屬時代的一切運動;他應當是一個小說家、一個記者、一個常人、所有事物背後的客觀存在、黑夜與沉默的代言人。
對霍夫曼斯塔爾,以及對巴特和布朗肖而言,當代詩人——或者作家——最終,徹頭徹尾是他所屬時代的產物,並為現代所浸染,而且,自相矛盾的是,他是一個放棄歷史的人,他將裝飾視為他所處時代之樂事,因而將其當作是歷史的誘惑而加以排斥。巴特的第一篇關於悲劇的文章,其意義不在於時間,而在於“一個即刻的,被拆除了時間大門的宇宙”。在此文中,現代作家是一個進入既不短暫也無歷史性的夢境或者悲劇的人。(在《羅蘭·巴特自述》中,巴特發現,從歷史上講傅立葉要比福樓拜重要的多,即便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他的當代史的直接痕跡”,然而“福樓拜在小說的整個過程中敘述了1948年的所有重要事件”。是,傅立葉直接表達了歷史的欲望。)尼采與巴塔伊感覺,現代人的困惑形成於我們身處歷史的盡頭這種想法。
如果將《寫作的零度》當作似乎它隻是完全沉浸於薩特式的信念來閱讀的話,那就會出錯;同樣,如果完全以神秘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巴特也會是一個錯誤。這種視角會使人輕易推斷出巴特與布朗肖之間的同源關繫。我無意於在巴特與布朗肖之間作出強烈的對比,在所謂文學宗教方面他們二人無疑是有共同之處的,但我更願意以波德萊爾提到畫家的性情時的方式指出他們在氣質方面的不同。從學識以及文學上來看,他們同屬於一個運動,一首當代天鵝的文學之歌。但是從風格的角度來看——作為作家身體的那個風格——布朗肖具有那種神秘主義的氣質,巴特則具有現實主義氣質。我們甚至能在此重申散文與詩歌之間的不同:布朗肖深受德國詩人的吸引,與他不同,巴特卻從不與詩人共事,他最愛研究的領域是19世紀的法國小說。在下兩章我們將討論現實與現實主義對巴特產生的問題,以及他毫不松懈地努力尋求一種近似於傳統小說或者評論文章的散文類型——或者是這兩者的混合體。巴特堅持認為,零度或者白色寫作雖然成功地表達了現代人的空虛以及文學的終結,但它們也會因為變成一種刻板印像或者一種陳腔濫調而終止。因而,他阻止了沉默的絕對論,打破了它美麗而殘酷的神話,以及它消極的順從。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小心翼翼地並且毫不聲張地支持一個積極的價值,即便如我所言,書中的基調是悲劇性的:我指的這個積極的價值就是意志。寫作是一種意志的行動,尤其在幻想破滅的時候意志需要更加堅強有力。
此外,文學已變成一個語言問題這一事實也打開了新的視野,“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巴特說道,在其中也許“作家的理性與人類的理性之間會重修舊好”。自1830年左右資產階級寫作的到來開始,法國文學拋棄了崇高的古典規範,試圖去再現人們所說的,以及生活中使用的各種語言,並在此過程中大量繁殖,因而,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個體的全部本質都與其語言等同一致。 寫作的意志是一種工作形式:工作作為《寫作的零度》中所有一切的背景與基礎而出現,並不僅僅因為在1850年左右,整個作家階層迫切地要擔當起他們傳統的全部責任,讓寫作的工作價值取代其使用價值。寫作將因它所付出的勞動而非它存在的理由而得到拯救。現在,作家作為工匠的形像開始盛行,他將自己關在某個傳說中的地方,像個在家做活的技工一樣,先大致勾畫出作品,再切割、拋光,就像一個寶石匠一樣從原料中提取藝術,設置他的形式,每天他都要定時孤寂地為工作付出辛勞。
工作也被視為欲望,是西西弗斯般無望的勞作,及作家的專業技能。事實上,我要說的是寫作的意志,那種痛苦、犯罪感以及烏托邦,簡而言之,現代作家的那種整體的模糊性代表了一種真實而典型的工作現像論,在其中,主、客觀事實被融合,進而混為一體以克服個體與社會間的分裂。後來,巴特將以一個題為《整體怪物》的片段結束《羅蘭·巴特自述》:“不同的話語:今年8月6日,鄉下,一個晴朗天的早上:陽光、溫暖、鮮花、沉默、平靜的、容光煥發。什麼也沒有激起,既沒有欲望也沒有侵犯;隻有任務在那兒,我面前的工作,就像一種無所不在的存在:每一件事都是飽滿的。那麼,那就是自然?一種……剩餘的缺席?整體的缺席?”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一個人若要研究一位作家就無法回避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什麼是評論——尤其是當被研究者本人還是一個評論家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迫切。人們總想得到一個明確、可靠的答案,將其用作研究的起點,最好還能同時用作終點。當然,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因為文學評論以另一個相關的問題為中心,這個問題是它的又一個翻版,並對它起著指導及調整作用:即什麼是文學?但文學就是¬——一直都是,而且終將還是文學評論的翻版。
正是這種質疑無果的經歷促使我決定從《寫作的零度》開始研究,在本書中,巴特剛涉足評論事業,他竭力尋求文學的定義並明確表達他的寫作概念。
在我寫作的時候,問題逐漸變得非常具體。確定了一個最初的主題或者主旨後,在某個時刻,我意識到頁數在膨脹,而論點的證明則依賴於各種想法與碎片的交織來進行:諸如對某個文本或者作者清晰無誤的引用,一些句子以其優美的樂感打動我,或者因為它們在一繫列論證中起到至關重要的連接而引用。我也不確定到底孰先孰後,是批評釋義呢,還是這些炫目的靈光閃現。這真的無關緊要:這也是我僅有的一次認為閱讀與寫作是可以重合的。在真正決定寫作之前,在寫作的欲望成形之前,這種重合可以和閱讀與寫作之間深刻的分歧同時並存。
在這個寫作的意願上我欠羅蘭?巴特一個人情,但我欠他的不是方法,也不是一套概念—— 這些我在別處都能找到——而是一種態度,一個道德觀念。不是知識,而是意願。在《就職演說》中,巴特說道:“智慧不是權力,而是一點知識、一點學識,還有盡可能多的情趣。”
羅蘭?巴特:我心目中的大師。我喜歡用這個過時的名字稱呼他。幾年前在巴黎導農大街舉辦了一場維也納建築師阿道夫?路斯的作品展覽,他在那個研討會上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我再次參觀了我們這個小團體過去時常會面的場所,它現在已經面目全非,變成了一個畫廊。研討會上的得意忘形,羅蘭?巴特自己也曾多次對此評論——是友誼的信念,是文學的信仰。
我還記得1978年10月或者是11月期間,羅蘭?巴特在紐約大學一間巨大而人滿為患的禮堂裡侃侃而談的情形。他談到了普魯斯特以及他自己要寫一本感傷的小說的打算。這是出乎意料的講座,完全不同尋常,就像預言在現今世界一樣——或許,甚至像個人宣言一樣少見,尤其是當它們全無絲毫情感在內的時候,因為我們已經如此習慣了專業性和編碼語言。
那個房間和他的嗓音,加上他成功者以及孤獨的形像構成他這個略帶羞澀的人。我並沒有傾聽這個可謂是上佳的講座,一次絕妙的學術表演,但我體會到了當時的時間與空間以及真言的意義。
我無意寫文章表達對巴特的敬仰,也不想寫關於巴特或者結構主義,或者其它任何一類的學術運動的綜合研究(已經有好幾種此類研究了,而且其中有兩個取得非凡的成果:一個作者是安妮特?拉維爾,另一個是斯蒂文?昂加爾)。我想聚焦於在我看來是當代文學與評論中巴特最與眾不同的特質,這就是他對文學,以及對文學命運的關注,而在當今世界幾乎已沒有文學的立足之地。這也是為何我沒有采取紀年表的方式,或者論述他所有的著作。我堅持要論述他的一些著作,但忽略其他一些著作,即便它們是他最負盛名的著作,而且為文學研究開啟了新的途徑(例如《論拉辛》和《S/Z》)。我對巴特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無甚興趣,這是一種標新立異的故作姿態。我要說的是,我更感興趣的是結構主義的失敗,是巴特如何使20世紀60、70年代的科學夢想失效。我認為在今天強調文學思想的宗譜是值得做的,這顯然將巴特與19世紀的幾位法國作家及普魯斯特聯繫在一起,而且幾乎出人意料地與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這樣的作家聯繫起來,在世紀之交,霍夫曼斯塔爾表達了一個深刻的歷史危機和他個人對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惆悵。自波德萊爾和福樓拜以來,一種模糊性決定了現代作家,或者具有現代性的作家,我將巴特視為這種至關重要的模糊性的一部分。這種模糊性存在於對某種新鮮的、不同事物所具有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中,它與過去決裂,而同時無可避免地蔑視當代世界,還有那所有讓我們產生錯覺,以為自己屬於什麼事物的空談。
我想要追溯那種模糊性的模式,它既是形式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模式。巴特在一個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態度之間搖擺不定,在新的修辭與傾向於過去之間猶豫不決。我研究貫穿巴特事業始終的悖論,不是為了對他進行評判。用巴特的話說,悖論本身難道不是一種表達情感的修辭手段嗎?在我們喜愛的作家中,或者是我們痴迷的句子中標記出悖論,這意味著要讓他們免於遭受公眾的觀點意見的口誅筆伐。這是些庇護性的言辭,使其不被流傳,免於墮落,或者被貼上具有還原性的,固定的標簽,雖然有時需要它們來達成某種基本的理解。我們總是在簡化的需要——為了使事情清晰明了——與事情總是極其微妙、復雜、精妙的認識之間撕扯。遵從悖論就意味著要意識到,總體而言,語言一方面太貧乏而同時又太豐富。正如布朗肖所言,矛盾是“文學活動的現實”。
我在第一章中討論的第一個悖論有關一個老生常談,它似乎依附於結構主義的接受:即歷史相對主義和形式主義是對立的假設。相反,我認為自從開始文學評論以來,巴特就非常關注歷史問題,而且幾乎痴迷於此。出於此原因,我認為《寫作的零度》盡管是他早期的著作,卻依舊是理解他獨到的形式主義的根本。巴特隨後研究了歷史與作家之間的關繫,歷史被理解作是他自己所屬的時代與文學的歷史,而他的第一本著作已經包含他隨後研究中所有重要的主題。我還要強調他的另外一本不太受到關注的作品的重要性,這本著作幾乎是與《寫作的零度》同時代完成的,即《米什萊》,它直到1987年纔被翻譯成英文。奇怪的是,在早年期間,巴特開始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產生興趣,卻發表了研究19世紀歷史學家的專著。在後面,我將盡力確定他對米什萊持續關注的含義,他的這種興趣一直持續到他最後的一部著作《明室》,我將在第三章中討論本書。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張力展示了一個表現、描述問題,該問題時常縈繞在巴特以及我們整個一代人心間。對攝影的興趣使對這同一問題的分析更進一步。
我用了一個很直率的陳述來定義巴特的第二個悖論,這也是第二章的標題:“對抗語言”。這些詞語極大地挑戰了人們在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時代裡最普遍的刻板印像,也就是,一切都是語言。我在本章中要將巴特看待語言的不同的,甚至常常是矛盾的態度交織在一起。在這一方面,人們應該堅持關注他1978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說,以及我所謂的評論悲劇,它展示出強烈的悖論:就在巴特賦予“符號學”這一個新的學科以相應地位的時刻,他公然拒絕其科學上的裝腔作勢,宣告了語言的“法西斯主義”,並表達了他對文學一種鄉愁般的愛戀,而且還是以近似於普魯斯特美學的詞語表述的。
在第三章,關於巴特對現實主義的遲疑又將我們帶回到他和普魯斯特的密切關繫中,這在《明室》中尤為明顯。可是,我認為巴特贊賞的,他為之投入激情的,以及為他所認同的作家與其說是普魯斯特,毋寧說是米什萊,那個卓爾不群、毅然決然對抗他所處世紀的作家,那個談到愛的作家。伴隨著米什萊、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張力開啟了我的考察,又作為結論回到原地。雖說巴特大談特談他創作小說的欲望並引起了人們的翹首以盼,可是我認為《明室》是他唯一“能”寫的一本小說,或許,他想寫的是篇散文,在其中對攝影的批判性分析與對時間和死亡的凝思在一個非常個性化的研究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我對批判性寫作的理想是:它應該同時具備以下特質:通俗易懂、能夠駕馭知識、構建一個論點,它是熱烈的,能夠被打動的,因而它的情感纔能滲透出來(人們可以說,它應該既具有一個聲明的力度,也具有一句話語的力度)。雖然可以允許它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但應該像古典建築一樣明朗、和諧。它應該反映並且吸收思想、解釋、以及情感後面的生命力。這難道不是隨筆的定義嗎,羅蘭正是在其生命末期創造出這個形式,我相信,它將作為過去二十多年裡最有趣、最美麗的一種文學表現形式之一,並超越脆弱不堪的學術風尚而繼續存在。 查看全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