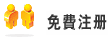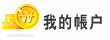內容選登:
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10月(1935年)
魚化石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化於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地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
(1936年)
馮文炳選集》序
人民文學出版社特約了馮健男同志為他叔父編一卷《馮文炳選集》,要我在卷頭寫幾句話。這又是我作為後死者義不容辭的任務,且不論我夠不夠資格來擔當和勝任與否。健男同志先曾找我懇談過,提出了這個建議。的確,和他叔父歷史較久的文學界相識,尚在人世的已寥寥無幾,俞平伯、朱光潛等老先生都年逾八旬,就算我這個七十四歲人*年輕了。
廢名生前,特別在抗日戰爭前,好像與人落落寡合,實際上是熱腸人。我在1933年大學畢業期間,在沙灘中老胡同他住處和他第一次見面,從此成為他的小朋友以後,深得他的盛情厚誼。他雖然私下愛談禪論道,卻是人情味十足。他對我的寫作以至感情生活十分關注。1937年1月我從青島譯出了一部長稿回北平交卷,就寄住他北河沿甲十號前後兩進的小獨院,用他內院兩(小)開間起居室一角的一張床。他寒假回南省親,留下一個老僕看守,也預先允許我讓萊陽回北平的何其芳(可能是回萬縣一行的中途)在他家和我一起住幾天,就用他內間的臥室。不久我也南歸,未再北返,北平淪陷了。全面抗戰爆發後,我到內地,轉輾各處,從成都到延安,從太行山到峨眉山,*後在昆明教書六年,隻知道廢名早回了黃梅家鄉,情況和地址不詳,八年失去了聯繫。直到1946年,我隨南開大學復員北返,纔在北平見到他一兩面,見到他十分高興。後來我應邀去英國,從天津到牛津住了一年半,北平解放,我回國到北京大學教書,見到他更興高采烈。但是當時我們不同繫,大家都忙,很少接觸。1952年夏院繫調整,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和外國文學所前身),當時正在籌建期間,我得機參加中國作家協會集中學習,然後下江、浙農村參加農業合作化試點工作近一年。廢名北調至吉林大學。我們從此未再見面,由於我一向懶於寫信,也未通音問。他病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事後很久纔聽說,更不清楚他的卒年月日。我們相處的日子實在有限,彼此也不相尋問身世,所以我本來不大知道他早年和避居家鄉期間的生涯,也不大知道他的晚景,隻是總信得過他的晚節。
廢名過去似乎極贊賞陶淵明所說的“讀書不求甚解”;我則天生不是做學問人,讀書不求甚全。即使個人偏好的古今中外大小作家,我沒有讀完過全集,隻有莎士比亞原文著作可算是例外。抗戰期間,我以在大學教書當職業了,在這條路上不得不向上爬,纔對有些專題多讀了一些書,得魚忘筌,也就當敲門磚拋開。1952年我從講堂轉到學院,總得做研究工作了,我纔先下鄉也帶了一卷本莎士比亞全集,在插手奔忙農村生產“組織起來”的工作,時期較長,總有餘暇,第一次讀完了全部,回來纔反復從面到點,參閱各家評論和提供的考證材料,算是鑽研了兩年(至於《紅樓夢》、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小說、巴爾扎克等單部頭長篇小說名著,當然不可能不讀全)。廢名的小說詩文,除了《莫須有先生傳》,我本來也沒有讀過多少。
現在健男同志精選了廢名近三十萬字的各類著作,並對他的生平作了較詳的介紹,我就又情不自禁,不惜在亟待完成的本職工作及其他社會義務等交迫的困難條件下,見縫插針,通讀了稿本,借以加深認識,溫故知新。
回想起來,我的已故師友中,有兩位為人著文,幾乎處在兩極端。而我和他們的私人關繫和對他們寫作情況等的看法,由此及彼,首先就有些難解難分的地方。這也許不免出人意外吧。
我都是在南邊中學時代就讀過他們二位的一些作品:徐志摩的第一本詩集(線裝仿宋字體本);廢名的一些早期短篇小說。大約1930年廢名和馮至同志辦《駱駝草》(開本像早期《語絲》的小刊物)。我出入北京大學第一院(即今舊“紅樓”),在大門東側小門房,每期必買(一期隻花),開始欣賞其中經常刊登的幾章《橋》或《莫須有先生傳》及別人的一些詩文。
廢名比徐志摩小五歲,我又比廢名小九歲。徐在1916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學讀過書,廢名現在知道1922年暑後就上了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來進了英文繫,中途輟學,到1929年暑前纔畢業。我恰好正是1929年暑後北上進了北京大學本科,也是英文繫。所以我們三人也可以說是先後同學。徐1922年回國,好像也在北京大學講過一點學甚至授過一點課,廢名想來沒有聽過;他還剛進預科。徐在1931年初北來北京大學英文繫教書,也就教到了我,我應稱是他的“及門弟子”,隻是僅到當年11月19日他就坐飛機失事去世了,他要新月書店出我一本詩集,也就告吹。其間他經常奔忙於平滬之間。我在班上見到他和偶在教師休息室門口和他面談幾句,通過幾次信,隻有一次約在地安門內米糧庫他所寄寓的胡適家客廳側室晤談過一陣。廢名和我相識較晚,是在1933年5月我出了一本小書以後。他和我卻交往較久,雖然抗戰期間八年失去聯繫,後來也曾有一年半隔在海內海外,*後十幾年分處關外關內,信都未曾通過,想不到也就從此永別。徐志摩寫給我的一些短簡上有時客氣地稱我“弟”(實亦即“弟子”),廢名對我從不應我稱他為長輩,給我寫信,總還稱我“兄”。他對我卻也是親切的,大約見我入“道”無緣吧,就送過我一部木版《庾子山集》(這部書現在早不知去向了)。
徐志摩纔氣橫溢,風流倜儻(雖然從小戴近視眼鏡),因是名家,照片流傳甚廣,確就是那個榜樣。他出身於浙江硤石大鎮的富商(現或可稱民族資本家)門第,留學美、英,特別在文化界上層,交遊極廣。相反,廢名是僻纔,相貌“奇特”(似為周作人語),面目清癯,大耳闊嘴,發作“和尚頭”式(非剃光),衣衫不檢,有點像野衲,說話聲音有點沙嘎,鄉土氣重。我初進北京大學,老同學中常笑傳他用毛筆答英文試題。他們兩位和我從不曾談及彼此。我可以設想,如果廢名見過和聽過徐志摩的外表和談吐,也會像魯迅一樣的不會喜歡,雖然他極稱賞他的一位舊同學,不久比徐志摩更早夭的年少翩翩的梁遇春(秋心),贊賞他的纔華、他的文采。北京大學過去曾有過聞名的兩派,《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徐志摩傾向於前者,廢名接近後者,也很自然。抗戰勝利後,廢名回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書,作新詩若干講,我當時在國外,不知其詳,近年來纔知道他關於我也作了一講,開頭竟說,本來應該講一講徐志摩,見了我的《十年詩草》,講了我,也就可以不講徐志摩了。廢名對徐志摩的偏見,從此可見一斑。
徐志摩在思想上是大雜燴,前後也多變,變壞變好,都有表現和苗頭。廢名在解放前,特別在抗戰前,似曾以他獨特的方式,把儒釋道熔於一爐。我記得1937年初在北河沿他家寄住期間(在他回南以前),曾認真對我說他會打坐入定,就是沒有讓我看過(他想必是在左邊一頭臥室裡做的功夫)。而他向我一再推薦過《論語》,把孔子和孔門弟子的交往及其言行,一掃腐儒的玄化,解釋得非常平易近人。他本來一直尊敬周作人,抗戰前出過四本小說集和長篇小說,都請他寫序。但是全面抗戰起來,他就和他的“知堂先生”分道揚鑣,自己從敵占的北平跑回南邊的家鄉,又甩脫打到家鄉小縣城的日本侵略軍,到山村教小學、中學,稱賞農民倒都有“日本佬必敗”的信心,聽到他們贊揚難得到境的新四軍,同農民一起深惡國民黨“苛政猛於虎”。他不怕外患,但恨“內憂”,敢於在抗戰勝利後公開發表的文章裡提說,還出於激憤說中國歷朝亡國都亡在一部分讀書人手裡。1949年春我從國外回來,他把一部好像詮釋什麼佛經的稿子拿給我看,津津樂道,自以為正合馬克思主義真諦。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頓悟”,又初回解放了的北平,認真做業務授課,又主動做學習補課,也正逢“大忙季節”,無暇也無心借去讀,隻覺他熱情感人。隨了日子的過去,現在從他後來寫的文章裡可以看出,應說是主觀上全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熱忱擁護社會主義,甚至有點從左到“左”了;他在課堂上,在專著裡,也顯得理所當然的對魯迅傾倒得五體投地。徐志摩三十六歲就去世,很難說他日後會有怎樣的思想變化;廢名的思想變化可就有這麼大。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不管人為的吹捧與貶抑,熱鬧一時或冷清一時,徐志摩富有詩意的散文、廢名也富有詩意的散文化小說,藝術上都別具一格,一筆勾銷,就有違歷史唯物主義和借鋻教導。平心而論,徐文不如徐詩,馮(廢名)小說遠勝馮詩,此所短彼所長,不能相提並論。兩者在這方面截然相反中,卻也有一些相通處。同是南中水鄉產物,詩如其人,文如其人。徐善操普通話(舊稱“官話”和“國語”),甚至試用些北京土白,雖然也還帶點吳方言土音,口齒伶俐、流暢、活栩,筆下也就不出白話“文”。馮操普通話也明顯帶湖北口音,說話訥訥,不甚暢達,筆下也就帶澀味而耐人尋味。徐文“濃得化不開”,馮文恬淡。兩人為文,有時候(馮在中期小說創作中)卻同樣會東拉西扯,思路飄忽,意像跳動,一則像雨打荷花,一則像蜻蜓點水。他們都像我的老一輩人一樣,從讀四書五經出身,徐、馮似乎都不喜唐宋八大家古文,在各自的寫作裡可以推測,徐傾向於楚辭、漢賦、六朝駢儷,洋洋灑灑,堆砌、排比;馮自己說推崇魏晉六朝文,但從他喜歡《詩經》、《論語》、五古等看來,肯定會喜歡《世說新語》一路文字,偶出撚花妙語。年來聽說有人研究廢名散文化小說,說有現代西方“意識流”筆法,我認為也許可以作此類比,卻不能說他受過人家的影響。徐志摩當然讀過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盛行過一時,到20年代登峰造極,或多或少影響到,影響過西方各派的現代小說家,也讀過意識流小說老祖宗英國18世紀小說家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自己還顯然有意識仿現代英國20年代意識流小說家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廢名肯定沒有讀過,詩文如有西方所說“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則中國古詩文也早有這一路傳統手法。徐馮二位同好契訶夫小說,徐當然更愛契訶夫的英國現代“高雅”(high brow)文士版的凱瑟琳·曼斯斐爾德(“曼殊斐兒”),馮則未必傾心甚至讀過她。他們在19世紀下半期到他們當代的西方作家中,卻也有同好——哈代。徐受過哈代詩的一些影響,馮則當然是喜愛哈代的鄉土小說。說來也怪,都不顯出有多少影響,徐卻譯過法國波德萊爾的一首詩(發表在早期《語絲》上,所附的一些廢話,受到魯迅的鄙夷),現在從廢名遺文裡知道他竟也讀過一點波德萊爾。當然他在西方文學大家裡*推崇的還是莎士比亞和寫《堂吉訶德》的西萬提斯,那就毫不足怪。
廢名小說創作是他留給後人的文學遺產的精華。他的早期小說也可說是鄉土文學。早在他以前,新文學史上第一大家魯迅早期一些小說就已經開了鄉土小說的寫作先河,誠如健男同志所說,廢名也不過是受其“啟迪”和“滋養”的一大群小說家之一。這種小說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城鄉自然經濟衰敗的社會底層小人物、農業勞動者等為主角或重要人物,出於同情,或念其淳厚不變而含悵惘,或傷其無知不爭而冷嘲熱諷等等,用平凡、庸俗以至鄙陋的事物材料作出別有一番風味的風俗畫或“浮世繪”。魯迅是大家,廢名是奇纔,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即使對比一下,也能發人深省。魯迅也曾看出過廢名的“特長”,說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裡,“以衝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魯迅早期寫鄉土小說,筆墨凝練,好像進行鈾濃縮,早有火藥味;廢名早期以至到更爐火純青時期,寫小說卻像蒸餾詩意,清甚於水。他同魯迅早期的一些小說一樣,以南中水鄉為背景(他以內地的湖北,不像魯迅以近海的浙東,歷史環境恐也有發展先後不同的因素),卻寫成了田園詩。他的小說裡總常見樹陰,常寫樹陰下歇腳,所以正中由厭惡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軍閥統治,到厭惡政治以至*後不免“下水”的周作人的下懷——他不是早已老愛捧苦茶在樹陰下坐坐嗎?周作人說廢名寫小說並不逃避現實,廢名晚年自己懺悔逃避現實,客觀事實恐怕卻證明他的小說創作也還是反映現實的,隻是反映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在小說裡(詩裡也一樣)常無端插入以點概“宇宙”“世界”“天下”之類話,好像(實也真是,不過從自我出發)以天下為懷了,認識不深,難於捉摸,有“哀愁”倒是可稱“無限”,像西方19世紀末一些探索無門的詩人愛用這個誇大的形容詞一樣。所以經過“吶喊”“彷徨”,視域擴大,認識深化,發展到30年代的戰鬥者魯迅,就說廢名“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滿他“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有意低徊”等等了。
分出的兩條道路,卻也有或直或曲,平行發展的階段。魯迅晚年大寫手榴彈式雜文、火花怒放的時期,也正是廢名放筆寫《莫須有先生傳》的時期。《莫須有先生傳》寫得好像很順手,卻不是水到渠成,而漶漫無涯。廢名喜歡魏晉文士風度,人卻不會像他們中一些人的狂放,所以就在筆下放肆。廢名說西萬提斯胸中無書而寫書——《堂吉訶德》,他自己實真是這樣寫《莫須有先生傳》。他也可以說寫他自己的《狂人日記》。他對當時的所謂“世道人心”,笑罵由之,嘲人嘲己,裝痴賣傻,隨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並列,例如我還記得《莫須有先生傳》有一章開篇就說“莫須有先生腳踏雙磚之上(北方城鄉土俗,窄溝茅廁兩旁置雙磚墊腳,今仍十分普遍),悠然見南山(陶潛名句)”。廢名的“哀愁”當時也還“有限”(實即不著邊際,不切時弊要害),但是也自有他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就他獨特的純正藝術風格而論,廢名的小說,應以《橋》上卷為高峰。《莫須有先生傳》是他另一個小說寫作奇峰,應說是他的小說絕筆了。他後來宣布不再寫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嚴格說算不得小說,早已結束鉛華,記事實、發議論,也就已經顯出了他的思想和文風早在抗戰八年裡“閃露”的轉機。
廢名寫過詩而且偶爾還寫詩,我是在30年代中期纔知道。他應算詩人,雖然以散文化小說見長。我主要是從他的小說裡得到讀詩的藝術享受,而不是從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詩。他的前期短篇小說和《橋》的一些篇章真像他自己所說,學唐人寫絕句。隨便舉例說,他在《桃園》這個短篇小說裡有一句“王老大一門閂把月光都閂出去了”。這就像受過中國古典詩影響的西方現代詩的一行,廢名卻從未置理人家那一套,純粹繼承中國傳統詩的筆法。他的分行新詩裡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難辨,層次欠明,他的詩,語言上古今甚至中外雜陳,未能化古化歐,多數場合佶屈聱牙,讀來不順,更少作為詩,盡管是自由詩,所應有的節奏感和旋律感。過去徐、聞(一多)一派詩,別的不說,在他們成熟時期,多數場合,運用口語干脆利落,雖然自有其語言音樂性,“站”得起來,並不“躺”在那,拖沓平板,即使今日有些詩人盡量用所謂“大白話”,除非用並不“普通”的“京片子”的地方,還往往是白話“文”。我自己寫新詩,經過一段曲折道路,刻意在實踐裡也學習這一方面,還感到難企及這兩位師輩的這種語言藝術優點。至於懂不懂,我敢肆言至今實際上還不曾好好解決“普及基礎上提高,提高指導下普及”的問題。過去白居易詩,“老嫗皆曉”,恐怕也是誇大說法。另一方面,“詩無達詁”或者可成一說。但是我盡管了然中國古典詩(詞、曲等)以及民歌的一種主要傳統,詞句盡管隨思路跳躍,有如現代西方詩,盡管含義甚或借用西方現成名詞來直稱中國古已有之的像征意義(或如今日所說的“潛臺詞”)可以層出不窮,思維總有邏輯,表層的有形語言,總該不含糊,應不招人各一解。中國文言,自有語法,實在有時比白話,更和西方語法*簡單的(但也用起來大不容易的)大語種英語倒更多相通處,隻是我們的省略(understood)法較多。詩如此,散文也如此。廢名對我舊作詩的一些過譽,令我感愧;有些地方,闡釋極妙,出我意外,這也是釋詩者應有的權利,古今中外皆然。隻是知我如他,他竟有時對於其中語言表達的第一層的(或直接的)明確意義、思維條理(或邏輯)、縝密語法,太不置理,就憑自己的靈感,大發妙論,有點偏離了原意,難免不著邊際。可能現在是我頭腦刻板,倒有點像呼應了西方古典主義的(不是古典名詩的)從嚴要求。我也從不反對從西方引進的有韻或無韻自由體或從中國“長短句”“七言古風”等繼承發展出來的自由體白話新詩,也曾常寫,現在如有餘力,也還願意寫,但是想總該協合中國傳統或一種重要傳統的特色,要求精煉,盡可能用說得上口的活的語言,寫與散文節奏上有別的詩行。一方面新格律探索,也很重要,那又當別論。雖然過去我一直尊廢名為知己的師輩,辱承他賞識和關懷,認作忘年的知交(不在乎常在一起,常通魚雁),我在這裡對他的詩與詩論坦率發表我的不同意見,就算是批評吧,他若尚在人世,我敢信決不會見怪。
廢名論詩如此,其他從他獨特的實踐中產生的文學理論,依我看來,也大有可商榷處。他從不趨時媚俗,嘩眾取寵,從不知投機為何物,所以他晚年激進,決不是風派,卻有時一反自己過去的作風,不加自己的獨立思考,幾乎“聞風而動”,熱腸沸湧,不能自已,於是乎舊時的妙悟、頓悟、擅發奇論甚至怪論的思想方法一旦與感人的新事物結合,我看不免有不少離譜的地方。他不幸沒有活到古稀,現在不像我老而不死,還得學到死,反比我年輕得多,我回顧他晚年的一些議論,反倒覺得天真可愛。話雖如此,他晚年論魯迅、論杜甫,卻也不時“閃露”一些真知灼見,是經驗中人所能道,創作過來人所能道,非純學者所能道,亦非任何他人所能道。
說來也可能出人意料,作為小說藝術家的瀋從文老先生(隻比廢名小兩歲)產量不小的創作,我讀過不多。現經健男同志提及,纔知道他早年曾經自稱他寫“鄉下”作品“受了廢名先生的影響”。我認為所謂“鄉土文學”,不限於寫農村題材的文學創作,應說是帶地方色彩的創作,特別是小說,或者與所謂“(大)都會文學”相對立,我可以推而廣之說,不限於鄉鎮小邑,還包括過去日趨凋敝沒落的一些歷史文化名城,甚至包括一些大都會的帶有地方特殊氣氛的城郊。而且我更想說,這還決定在(角度盡管不同)共同基於同情心來寫社會底層小人物、各種勞動人民,以至貧苦無告者,甚至在大都市也罷。我贊同健男同志說這條路在新文學中的“開創者”,“隻能是魯迅”。廢名自己也是有意無意首先受魯迅的影響,也許受廢名直接影響的許多人,同時也多直接受過隔代“開山老祖”的熏染。人家說受廢名影響的一串名字,我不知道有沒有師陀。我這位老朋友特別在跑不出“孤島”從此定居上海以前的“蘆焚”時代的早期小說,我相信同時又兼受過廢名的影響。和廢名家庭出身不同的何其芳早期寫散文作品,似乎也受過他的影響,影響所及甚至超出《畫夢錄》的部分篇什而跨入了一點《還鄉雜記》的界線。我的現在還是老朋友的一位北京大學和廢名與我一樣的接班同學(一則同在1929年暑假前後,一則同在1933年暑假前後),論家庭出身和廢名更不同,在北京大學中文繫受過廢名批改過作文卷,後來在1936年1937年一度“玩票”寫過,用多種筆名發表過的一些散文作品中,少為人知,而至今耐讀的散文化小說或稱小品,也就有廢名式風格。我以上所舉三位年齡比我小一些,可稱同輩的知名和不知名,去世和尚在人間的中國新文壇“保留角色”和一時跑過龍套的票友過客,受影響不限於廢名,許多地方,特別在筆法上,受廢名獨特風格啟迪,起催化作用,我想無可否定。我雖然沒有研究過,廢名作為“偏將”的獨特影響,看不見的好影響,看來既深且廣,確會涉及不少人。
這就不得不又扯進我自己。
說來奇怪,有些民俗風習,分布頗廣。舊時民間,有時逢嬰孩夜哭頻繁、顯然有什麼病,出於迷信,也可能出於無錢求醫,常在行人來往的村口鎮頭,朝空牆上貼一張紙,上書四行“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過路君子念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這例如從“上江官話”區鄂皖邊的廢名家鄉到江口吳方言邊緣區我的出生地,都曾流行。1927年暑後我到上海浦東中學讀兩年高中,有一個假日散步到較遠的市郊小鎮、在街上也忽然念到了這樣四行,回校心有所感,就借此四行,習作了一個短篇小說,後來到北京上大學,就帶稿在行篋裡,以備修改。大約在1930年,我從《駱駝草》上讀到廢名的連載小說,大概是在《莫須有先生傳》的篇章裡,也竟讀到這同樣四行的“靈符”(大概吳方言“睏”字換了普通話“睡”字。我用筆名後來在北平一家文學副刊上發表,近年來找到發表文一看,總覺太幼稚,決定廢棄了),這是巧合。說影響或者過去讀過點廢名短篇,感染過那裡的一些氣氛,也沒有學過他的文字功夫。1933年我寫短詩《古鎮的夢》,卻有意在詩中戲用了廢名的一篇小說題作為一行。這與內容無關,除了同有南中水鄉僻地人物事物風貌、與廢名早期小說有些相通。1937年春,我在江南,在《淘氣》一首現代變體十四行西式中國口語詩裡,想到廢名小說裡提到過的南方共同的一種風習——頑童在牆上寫“我是忘八”之類叫行人讀了上當,得到啟發,以“我真淘氣”作結。至於讀廢名詩作中《寄之琳》一首,我個人非常感動,自然覺得詩寫得極妙。原文如下:
我說給江南詩人寫一封信去,
乃窺見院子裡一株樹葉的疏影,
他們寫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寫一首詩,
猶如日,猶如月,
猶如午陰,
猶如無邊落木蕭蕭下,——
我的詩情沒有兩個葉子。
詩末注寫作月日是5月8日,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年份應是1937,正是我在杭州小住的時候。我好像記得是我轉寄給上海戴望舒,發表在他主編的《新詩》“八·一三”前夕的哪一期上。他在北河沿甲十號住處內院裡似在磚鋪地中間有一棵小棗樹。我當年春初離開那裡不久,他寒假省親後北返,我可以設想他在正屋書桌前一個人沉思,忽然間瞥見窗外小樹的情景。我喜愛這首詩,因此在抗戰時期花三年業餘時間寫出幾十萬字草稿而早已作廢的一部虛構長篇裡,就借這幾行真詩大做了一番假文章,開玩笑中,如今回想起來自有難忘的摯情。
要我寫序,我也就拉扯了這麼些瑣屑回憶、這麼樣說長道短,信口雌黃,又像自我標榜,又像自我抒情,到此擱筆,深感不安。但冀這番嚕唣多少有助於讀者論者的理解與衡量廢名的著作。
198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