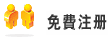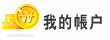韋勒克與他的文學理論(代譯序)
劉像愚
勒內·韋勒克(1903—1995)是20 世紀西方十分有影響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之一。他的八大卷《現代文學批評史: 1750—1950》歷經數十年之久,終於在生前完成,被文學界公認為“裡程碑式”的皇皇巨著;他與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出版近半個世紀,一直盛行不衰,先後被譯成20 餘種文字,不僅被世界許多國家的大學用作文學專業的教材,還被納入世界經典作品之列。對於這樣一位重要的理論家和批評家,我國的一些前輩學者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朱光潛先生在他20 世紀60 年代撰寫的《西方美學史》附錄的“簡要書目”中就列入了韋氏的《現代文學批評史》,並做了中肯的評價,稱其“資料很豐富,敘述的條理也很清楚”,但也指出了它對“時代總的精神面貌”重視不夠的弱點;錢鍾書在其《管錐編》中數次引用《文學理論》中的說法與中國典籍中的描述相互印證。1984 年,我們翻譯的《文學理論》由三聯書店出版,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書連續印刷兩次,發行數萬冊,使許多文人學者了解了他的理論。從那時至今的20 年間,《文學理論》被許多高校的中文繫用作教科書,還被列入中文專業學生閱讀的100 本中。然而,從80 年代末以後,此書即告售罄。目前,學界對此書需求甚急。於是,我們對舊譯略加修訂,交付再版。在書稿付梓前,對韋勒克其人其作似有必要做一個較為詳盡的討論。
一
1903 年,韋勒克誕生在維也納這座曾經培育了許多的音樂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文學家的文化搖籃裡。他的家庭成員都有很高的文化素養。父親勃洛尼斯拉夫·韋勒克祖籍捷克,從小喜愛音樂,是當地一名出色的歌手,曾經撰文評論瓦格納的歌劇,為捷克著名作曲家斯美塔納作傳,還翻譯過捷克詩人維奇裡基和馬哈的詩歌。母親加波莉爾出身於一個具有波蘭血統的西普魯士貴族家庭,能講德、意、法、英四種語言,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在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浸染中,幼年的韋勒克養成了嗜讀的習慣,他貪婪地閱讀文學、歷史、宗教、哲學、地理、軍事等多個領域的著作,經常欣賞歌劇演出,還學習演奏鋼琴。他在學校講德語,回家後講捷克語。從10 歲起,他開始學習拉丁語,在此後8 年的時間中,每周堅持閱讀拉丁文經典著作8 小時,閱讀了西塞羅、愷撒、卡圖盧斯、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塔西佗等名家的作品。從13 歲開始,他又學習希臘文,閱讀了色諾芬、柏拉圖、盧西安和荷馬的作品。在他患猩紅熱休學期間,他父親用德文為他讀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復學之後,他停止學習希臘文,同時開始學習英文,這一選擇為他日後長期的教學與研究奠定了基礎。
奧匈帝國垮臺後,韋勒克一家從維也納遷到古老的、充滿天主教氣氛的布拉格。在布拉格讀中學時,學校開設史地、拉丁文學、日耳曼文學、捷克文學等課程,但不開設英文,因此,他隻能在放學回家後讀莎士比亞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此外,他還讀了叔本華、尼采的大量論著。1922 年,他進入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學(即現在的布拉格大學)專攻日耳曼文學,學習語言、文學、比較民俗學等課程,還專程到海德堡聽當時以比較研究莎士比亞與歌德聞名的批評家貢多爾夫的講座。但是,大學課程中對他吸引力的卻是由著名捷克學者馬蒂修斯(1882—1945)主講的“英國文學史”。馬蒂修斯是布拉格語言學派的奠基人之一,像韋勒克一樣,也曾在奧地利度過少年時代,具有強烈的民族熱情,畢生致力於捷克民族文化的復興。他提倡一種簡潔、清新的文體,引導學生努力去探索、發明,但卻不贊成趨奉時尚和標新立異。他講的“英國文學史”完全擺脫了當時實證主義的影響,往往新意迭出,精彩紛呈。他的課程使年輕的韋勒克深受教益。他們師生之間建立了信任和友誼。在馬蒂修斯指導下,韋勒克如痴如醉地閱讀莎士比亞、浪漫派詩人和維多利亞詩人的作品;在馬蒂修斯雙目失明後,韋勒克則為他有聲有色地朗讀斯賓塞的《仙後》,聆聽他對斯賓塞不同凡響的評論。
為了準備《卡萊爾和浪漫主義》的論文,韋勒克於1924 年和1925 年兩次遊歷英國。當時的英國正處在對鄧恩、馬維爾等17 世紀玄學派詩人重新評價的熱潮中,這引起了韋勒克的極大興趣。就在這段時間內,他開始發表論文。篇文章是對《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一種捷克文譯本的評論。隨後的文章討論拜倫、雪萊和其他浪漫主義詩人。在馬蒂修斯的指導下,他完成了《卡萊爾和浪漫主義》的論文,提出卡萊爾反對啟蒙運動的武器是從德國浪漫主義那裡借來的新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1926 年,年僅23 歲的韋勒克獲得語文學博士學位。
在捷克的支持下,韋勒克第三次赴英,計劃完成關於“馬維爾和巴洛克以及拉丁詩歌關繫”的專著。但在牛津大學他獲悉法國著名文學史家皮埃爾·勒古伊正在撰寫一部論馬維爾的巨著,於是放棄原來的研究構想。後來,由於牛津大學的,他獲得國際教育研究所的幫助,於1927 年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參加了各種進修班的課程,但這些課程大都很難引人入勝,加上當時普林斯頓大學不授現代文學和美國文學,因此,他便轉而研讀門肯、凡·韋克·布魯克斯和新人文主義者巴比特和莫爾等人的著作。
此後,他在史密斯學院教授了一年德文,次年回普林斯頓,仍然教授德文,同時參加關於“黑格爾邏輯”的講習班。早先對卡萊爾的研究自然把他引向柯勒律治,而對柯勒律治的研究又不能不聯繫康德和謝林,於是他決定自己的第二篇論文寫“康德對英國的影響”。隨後,他取道英國回國,在大英圖書館仔細閱讀了柯勒律治《邏輯》的手稿,探索了這位英國詩人和批評家在借鋻康德思想中的得失。
1930 年秋,韋勒克回到查理大學,迅速完成了《康德在英國:1793—1838》的專著,並積極參加了布拉格語言學派的活動,他不僅在大學授課,教授英文,還把康拉德的《機會》、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等作品翻譯成捷克文,並用捷克、英、德等數種文字為許多雜志和布拉格學派的專刊撰寫評述理查茲、利維斯、燕卜蓀等劍橋批評家的文章。這個時期,俄國形式主義與捷克結構主義的理論引發了他強烈的興趣,他對什克洛夫斯基、雅柯布遜、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等人的論著格外重視。
1935—1939 年,韋勒克執教於倫敦大學,為布拉格語言學派文集第六卷撰寫了《文學史理論》的重要文章,在此文中他首次用英文評述了俄國形式主義和英伽登的現像學。而且在《細察》雜志上與利維斯展開論戰,批評他對柏拉圖以來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缺乏理解的錯誤。
1939 年春,希特勒的軍隊攻占布拉格,韋勒克此時失去了生活來源,但他很快獲得了美國學者的援手。持新人文主義觀點的愛荷華州立大學文學院院長福斯特馳書邀請韋氏任該校英文繫講師,韋氏夫婦途中在劍橋又停留了6 周,於當年9 月1 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當天住進了愛荷華城的一幢住宅中。
在愛荷華州立大學,韋勒克開了“歐洲小說”的課程和“德英文學關繫”的講習班,結識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其中往來密切的是奧斯汀·沃倫。當時的美國學界與英國學界大同小異,多數學者依然恪守老式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應該對傳統的方法重新認識,兩派之間在究竟應該重視歷史批評還是審美批評、重視事實還是觀念等問題上不時進行論戰,但雙方都缺乏理論上的自覺。韋勒克支持福斯特的新人文主義立場及其領導的改革,並力圖在理論上做出闡述,他修改並重新發表了《文學史理論》,出版了《英國文學史的興起》(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41 年),開始擔任《語文學季刊》的副編輯。
在這段時間內,韋勒克先後結識了“新批評派”的幾位主將:W.K.韋姆薩特、C.布魯克斯、A.泰特、R.P.沃倫。新批評派的理論給韋勒克留下深刻的印像,相形之下,他深深地感到新人文主義理論的缺憾,於是決定和奧斯汀·沃倫合作撰寫《文學理論》,重點討論文學藝術品的本質、功能、內部結構和形式等方面的特點,同時闡述文學與相鄰學科的關繫。這本書把俄國形式主義、捷克結構主義與英美新批評的觀點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由於戰爭,韋勒克中斷了與布拉格學派的聯繫,但他對理論的興趣卻有增無減。1944 年,他被提升為教授,次年夏天,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他與沃倫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進行了成功的合作,就《文學理論》的各個章節交換意見並完成了部分章節的寫作。
同年秋,他們返回愛荷華。這時消息傳來,他從前的導師馬蒂修斯在捷克獲得解放前夕去世了。他正打算回布拉格去繼承老師的事業時,耶魯大學表示願意給他提供一個教席。於是,他改變初衷,留在美國,並加入美國籍。這時,耶魯大學授予他榮譽碩士學位,邀請他參加“現代語言學會”會刊編輯部的工作。他被聘為耶魯大學斯拉夫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主講“俄國小說”。他深感這類課程的傳統設置與講法有先天的不足,因為在他看來許多不同民族的文學都有內在聯繫,特別是上承古希臘羅馬傳統的歐洲文學理應被看作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因此,文學課程的設置與講授應該從過去的國別文學擴展到超越民族界限的領域中。1947 年和1948 年的兩個夏天,沃倫來到耶魯,與韋勒克繼續《文學理論》的寫作。
1947 年和1948 年,韋勒克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做過講座。1948 年秋,耶魯大學建立比較文學繫,韋勒克被聘為首任繫主任,並成為當時新創刊的《比較文學》雜志的編委。在該刊第1期上,他發表了與阿瑟·洛夫喬伊論戰的著名論文《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觀念》,批駁洛夫喬伊認為西歐浪漫主義不是一個統一體的觀點。1949 年夏,韋勒克加入了J.C.蘭色姆、A.泰特和 Y.溫特斯等新批評派的行列,成為肯庸學院的研究員。這一年,《文學理論》出版,此後,他便全力以赴投入《現代文學批評史: 1750—1950》的寫作中。
20 世紀50 年代,韋勒克迎來了他學術生涯的極盛期。從此之後,他的著作、論文、書評、通訊以及各種文章源源不斷地問世,論述所向,遍及美、英、德、法、俄、意、捷、波等許多國家的哲學、美學、歷史、思想史、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思潮運動、文學分期、文體、方法等領域。
1955 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現代文學批評史》、二卷;1963年,美國的捷克藝術與科學研究會為他的60 歲誕辰出版了《捷克文學論集》,同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批評的概念》;1965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論文集《對照: 19 世紀德、英、美思想與文學關繫研究》,這一年,耶魯出版了《現代文學批評史》的第三、四卷;1970 年,耶魯出版了他的第四個
論文集《辨異:續批評的概念》;1981 年,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把他在該校的演講編為一集出版,題為《四個批評家:克羅齊、瓦萊裡、盧卡奇和英伽登》;1982 年,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把他20 世紀70 年代所寫的文章選編為一集,作為《批評的概念》的第二個續本,題為《對文學的攻擊》;1986 年,耶魯出版了《現代文學批評史》第五、六卷,1991 年出版第七卷,1992 年出版第八卷。
由於其博大精深的學識與出類撥萃的學術活動,韋勒克一生獲得了極高的榮譽:他被世界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羅馬大學、慕尼黑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除在耶魯大學任斯拉夫文學繫教授和比較文學繫主任外,他還兼任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印第安納大學、夏威夷大學和世界許多大學的講座教授;他曾三次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一次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多次獲得各種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博林根基金會的資助,還獲得過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出色服務獎等獎項;他曾經榮任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副主席(1964)、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1961—1964)、美國比較文學學會主席(1962—1965)、美國捷克研究會主席(1962—1966)等學術職務。他所教授過的學生中有許多已經成為當代的知名學者。
二
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是韋勒克畢生的事業。他的理論探索涉及文學本體(《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布拉格學派的文學理論和美學思想》等)、文學史(《文學史的理論》《文學史中的進化概念》《文學史的沒落》《英國文學史的興起》等)、文學批評(《現代文學批評史》《20 世紀批評主流》《新批評前後》《批評的概念》《辨異:續批評的概念》《俄國形式主義》等)和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的名稱與實質》《比較文學的現狀》《比較文學的危機》《康德在英國》等)等諸多領域。在文學批評方面,他發表了大量關於歐美作家、作品的評論,此外,他還對許多批評家及其論著加以批評,正因為此,他不僅被稱為著名的理論家和批評家,而且還被稱作“批評家的批評家”。
《文學理論》與《現代文學批評史》是韋勒克有代表性的兩部著作。
《文學理論》是從總體上對文學所做的理論探索,它包括了文學的定義、本質、功用、結構,以及文學研究的對像和研究方法等根本性問題,既有本體論上的意義,也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它與傳統的《文學原理》《文學概論》一類書的根本區別在於它的兩位作者深信“文學研究應該是‘文學的’”,因而他們區分了文學的“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並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文學的內部研究上。對文學研究做這樣的區分是《文學理論》的個重大貢獻。
所謂文學的“外部研究”側重的是文學與時代、社會、歷史的關繫,其理論預設是從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以來延續了數千年的“模仿說”與“再現說”,即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和再現。自浪漫主義文論興起之後,“表現說”更多地進入了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視野,但這種強調作家在文學創作中作用的觀點,依然是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的。
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從古希臘羅馬中經中世紀、文藝復興、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直到現實主義的各種文論,始終是圍繞著模仿—再現—表現這條主線發展的,批評家的眼光總是圍繞著文學外部的問題轉來轉去,唯獨不太重視文學本身。這種傾向在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論中發展到極致。文學理論家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文學應該如何典型地再現生活,如何更好地為時代、社會、政治服務,文學應該如何實現自己的教化功能等問題上;批評家們關注的主要是文學作品的內容、主題、人物和現實生活的關繫,文學藝術家們對生活的把握之類的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們緊步蘇聯文藝思想的後塵,不斷發展的依然是這條從外部切入文學的理論路線。這種在古今中外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側重外部研究的文學理論自然有它的道理,因為文學藝術不可能脫離與現實、生活、歷史、時代的緊密聯繫,文學藝術也不可能沒有教化作用。但問題的關鍵是過分強調這類關繫卻掩蓋和忽略了對文學藝術本身的理論研究,這就使文學喪失了文學性、藝術喪失了藝術性。
從19 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像征主義文論與唯美主義文論,把傳統的文論帶入了現代主義階段,進入20 世紀之後相繼出現的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等不同流派的文論成為現代主義文論的主流,它們一反傳統文論強調文學外部研究的思路,把研究的重心置於文學本身,它們要求高度重視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技巧、方法等屬於文學自身的因素,這就是雅柯布遜所謂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韋勒克與沃倫醞釀撰寫一本符合現代主義文論精神的理論著作,這就是20 世紀40 年代末在美國出版的《文學理論》。
2016 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