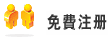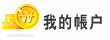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9655 商品編碼:10028567195186 代碼:172
"內容簡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阿根廷, 一個名叫克拉克的英國自然主義者(也是達爾文的親戚)來到潘帕斯草原上,目的是尋找一種傳說中既會跳又會飛的兔子。陪伴他的有一個少言寡語的高喬人向導,一個年輕的畫師,還有一匹馬。一行人首先來到了薩利納斯·格蘭德斯地區,卡福爾古拉酋長帶領著馬布切部落生活在這裡,克拉克很快發現這位酋長是通過故事和神話統治著整個部落。隨後卡福爾古拉酋長卻突然失蹤,這與馬布切神話中的故事不謀而合,克拉克和他的同伴們同意幫助尋找酋長的下落。路途中,克拉克又遇到了另外兩個與馬布切截然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深受歐洲影響的沃羅卡族和一個住在地下的部族。更令克拉克驚奇的是,印第安人的語言中每個詞都有至少兩種意思。身處語義含混的異域文化之中,克拉克發現自己的思維邏輯、科學觀念、進步思想甚至言行舉止都在阻礙這次旅程……
《野兔》再一次展現了艾拉式離題敘事的魔力,對愛、殖民主義以及語言的本質都有細微的思考。 作者簡介塞薩爾·艾拉(César Aira),1949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是當代頗有個人特色的西班牙語作家、譯者和評論家。艾拉從不在國內接受采訪,總是在咖啡館即興寫作,堅持在紙上寫稿,寫好的稿子從不修改。他的書大多是不足百頁的中篇小說,且善於從流行文化和各種類型文學中汲取養分,作品想像豐富,形式多樣,目前共出版有80多部小說、短篇集和評論性散文集。除寫作之外,他翻譯過大量文學作品,還在大學講授法國詩人蘭波和馬拉美的作品。 艾拉在西語文學界飽受贊譽,成為繼博爾赫斯、科塔薩爾等人之後備受推崇的阿根廷文學代表人物。2014年,艾拉入圍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短名單,次年又入選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決選名單。
精彩書評艾拉是拉美文學的杜尚。他是當代具有誘惑力、特立獨行的西語小說家之一,絕對不可錯過。
——娜塔莎·溫默,《紐約時報書評》
在艾拉的妙筆之下,含混積蓄為秩序,謎團得以澄清,每個看似離題的敘述至終都自有其目的。
——《出版人周刊》
讀完艾拉後,我往往不記得任何東西,就像大夢初醒時,驚覺夢中那些繁復的電影畫面消失了。
——帕蒂·史密斯《紐約時報書評周刊》
艾拉的作品是被投遞到平原上的密密麻麻、變幻莫測且結構精巧的建築物,不事張揚的抒情風格與他對由形而上學、現實主義、通俗小說、達達主義糅合而成的不協調組合的偏好,被調適得恰到好處。
——邁克爾·格林伯格,《紐約書評》
你真的應該到阿根廷南部去尋找那位當今西班牙語文學界具創新精神、令人感到興奮與震撼,也是具顛覆性的作家:塞薩爾·艾拉。
——西班牙《國家報》)
艾拉逾越了現實的邊界,世界不再辜負他的想像力。
——本傑明·萊塔爾,《紐約太陽報》
《野兔》使平淡、乏味的潘帕斯草原變得像愛麗絲所處的仙境一樣奇譎而多變。
——美國國家廣播電臺(NPR)
精彩書摘復闢派領袖羅薩斯渾身是汗水,眼睛睜得很大,跳下床,站在冰涼的瓷磚地上,雙臂像鴨子一樣晃悠著,抖動了幾下。他光著腳,身穿睡衣。原本十分白淨的被單,由於他在噩夢中的扭動而糾纏成一團;那是他銅床上唯一的被子,銅床則是他午睡用的小臥室裡唯一的家具。他拿起被單擦了擦臉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殘存的恐懼讓他感到心髒快要破裂了。但是,感官遲鈍的迷霧已經開始消散。他邁出一步,接著又是一步,整個足尖支撐在地上,渴望得到站穩的新鮮感。他走近窗戶,用指尖拉開窗簾。院子裡沒有人,隻有棕櫚樹和鉛一樣沉重的太陽,一片死寂。羅薩斯回到床邊,但沒再躺下;他思考片刻,坐在地上,雙腿伸開,挺胸抬頭。光著屁股能感覺到瓷磚的冰涼,感受到些許快感的衝擊。他收回雙腿,準備做鍛煉腹部的運動。雙手放在腦後,運動量可以再大些。起初,有些費力;後來,仰臥起坐的動作加快,反抗著地球的引力,同時他也在思考。順著思路,他做了一百個動作,每十個為一組,時刻都在思考。他一點一滴重新回想噩夢中的細節,像是一種自我懲罰。腹部運動的舒適感驅散了記憶中的恐懼。或者準確點說,沒有驅散恐懼,而是可以控制住恐懼,使體育鍛煉又多了一項成績。在午睡時刻光顧他大腦的這些幽靈總感覺還沒溜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些目不識丁的野蠻人,以為這是因為他所犯下的罪行的影子落在了良心上,這想法是多麼荒謬啊!那等於是倒著數數: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他的敵人之所以會這樣認為,是因為反對的立場會讓人從對立面看一切問題。真正讓羅薩斯感興趣的是那些他從未犯下的罪行,對此他感到非常遺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過去,他心太軟了,太講規矩了。他們說他是魔鬼,可他後悔在途中某個節點上失去了真正當魔鬼的機會。他後悔自己無法成為自己的對立面,那樣的話,他就能描繪出自己的兩種形像,就像一張精巧的雙面繡。一、二、三、四……他一向缺乏想像力,而沒有想像力,殘忍的計劃就不能完全變成現實。五、六、七、八……有人在那些自由派的小報上刊登針對他的指控,先是有一篇叫《吶喊》,後來又有《槍斃羅薩斯》(多麼愚蠢的名字),他夢中的形像卻與這些莫名其妙的指控恰好相反。世界顛倒了。除了文學一無所有。解開他夢之謎的鑰匙正是眼看生命流逝的遺憾。他缺少真正的創作纔能,缺少充滿詩意的靈活。九……通過與自己這樣坦率地對話,他意識到了這一點,為此感到失落。可是到底在哪裡、哪裡、哪裡纔能找到必要的本領,以便將蒙得維的亞那些雇傭文人筆下瘋狂的幻想轉化為現實、生活以及真正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東西呢?十,一百。 辦公室裡,秘書在寫字,羅薩斯喝掉半斤摻了冰水的杜松子酒。秘書寫完一行字,他喝一小杯酒,不算太多。看著別人寫字,讓他歡喜。他認為這是為數不多的有內在價值的活動,對觀眾幾乎沒什麼要求,除了一點點耐心,可他已經很有耐心啦,太多了,讓他覺得身體裡面再也裝不進別的東西了。他得等一會兒,口頭表達的內容纔能變成一頁書寫漂亮的文字。因此,他特別重視工整。似乎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是羅薩斯能看到兩人之間正在進行的信息轉換。在昏暗的辦公室中,他依稀看到一個幽靈的輪廓。人的動作總會創造出一個觀察事物的角度,如果是寫字的動作,就更是如此。手動,眼動,筆動,好似一個裝滿幽靈的皮囊膨脹開來。幽靈就是想把自己變成他者。羅薩斯透過一層發光的薄霧看著這一切,好像周圍所有的東西都籠罩在一片瑰麗的亮光中。這是因為他在炎熱的下午喝了酒的緣故,當然環境本身也有原因。他經常說,他發現杜松子酒加冰水是防暑降溫最有效的辦法;可他沒說,實際上他並不怕熱。總之,在熱天裡制造出對涼爽的迫切需求(或與之相反),也許會讓話語更有現實感,這辦法出奇地有效。這就是為什麼人類,具體來說是英國人,總能在談話中賦予天氣特殊的意義。那是世界中的世界的緣故,不是做戲,而需要去認真對待,相信它。或許這讓正在準備的酒水有了意義——冰水是為了降溫的,杜松子酒是為了增色的,沒有它兩者就無法真正融合,或者就看不出融合的跡像。一切問題都是在從一種狀態向另外一種狀態、從一種實體向另外一種實體、從一種可能向另外一種可能的轉變中解決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是他,而非別人成了復闢派。他就是如此,因為……因為什麼?不對,原因剛想起來,又以閃電般的速度從他大腦中溜走了。他聳了聳肩膀。理解的那一刻一晃就過去了。羅薩斯像木乃伊似的怔怔地站了好長一段時間,腦中一片空白。他唯一的動作就是舉杯喝酒。忽然,秘書把寫好的那頁文字遞給他,那些文字就是書寫工整的樣本。筆在另一隻手上,秘書請他簽字。 一天的工作剛結束——工作很輕松,到了近於無的程度——羅薩斯就去馬努埃麗塔為他煮馬黛茶的草棚下坐下來。這是與家人共度的親密時刻,他用來思考。他在思考,自相矛盾的是,大腦裡卻一片空白。這看上去不可能,但某人自視甚高,認為自己的大腦可以毫不費力地思考。好大一群鳥在唱歌,三四條狗在做遊戲的孩子們腿邊竄來跑去。在他身後,半圈檸檬樹在淨化著空氣;正對著他的,是一棵垂柳,枝條撥地而起,似乎是一朵野外的鮮花,有人故意放在那裡,討他的歡心。葡萄籐下是夯實的土地,為了迎接他的到來,有人在地面上灑了水。有時,在他什麼也沒想的時候,甚至以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男子,唯一真正活著的人。空氣中沒有一絲風,但是熱得並不過分。馬努埃麗塔是個丑丫頭,臉色蒼白,她從廚房到放椅子的地方來來回回地送著馬黛茶。她這位親愛的老爹,每次來這裡坐一坐,纔喝掉六碗馬黛茶,因此不必在戶外安放茶爐。他小口品茶,發出吧唧聲,她就站在一旁伺候。這位主張復闢君主制的領袖羅薩斯,並不覺得自己的寶貝女兒秀麗、聰明,他倒是相信女兒有點傻。又傻又笨,還很勢利。是的,馬努埃麗塔就是這樣。更糟糕的是,她缺乏樸實勁,沒有可加分的因素。她就是個沒心眼的木偶。他對朋友們說出這樣的心裡話:“她是我的壞習慣之一。”他喜歡這丫頭,但不知道為什麼。兩人之間有些誤會,這可以看出來,卻沒法弄明白。她堅信老爹喜歡自己。他常常納悶,自己怎麼會生出這麼個女兒來?幸虧父親經常是不確定因素,母親的因素則是確定無疑的。望著馬努埃麗塔的樣子,羅薩斯覺得自己是個女人,是母親。多年來,他一直琢磨著要把女兒嫁給艾烏塞比奧,一個瘋子。這是他的秘密心事,為不可能實現而暗自竊喜。不過,眾所周知,不可能之事往往是最x成真的。因此,後來有一天,當他看到那些野蠻人在漫畫諷刺詩裡談到這個嫁女兒的想法時,他困惑不已。事實上,關於這件事情,他從來沒跟人吐露過半個字。那些人不僅這麼寫出來,而且按照他們由來已久的習慣,都有圖畫配上文字。那些肮髒的野蠻人,當然會像所有的反對派那樣,隻能在《組合數字》雜志上運作,根據一些零星的線索妄加猜測,這樣看來,他們會得出“女兒加瘋子”的結論,也就毫不奇怪了。話雖如此,羅薩斯還是感到萬分驚愕,正如他所想的:我們能認清別人的誤解嗎?可是關起門來說,管他什麼自己還是別人的誤解呢!胡思亂想往往從兩個極端開始——從過分和缺乏制造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誤解開始。阿根廷政治統一派人士也許將羅薩斯嫁女兒的這個想法理解成了某種寓言:這個主張復闢君主制的家伙用一個裝滿臭屁的白痴充當獵槍,去“捕獵”國家政權。這裡,羅薩斯由於正字法知識不扎實,始終想不明白;但是也沒什麼要緊,因為對那些人來說是寓言,在他看來卻是事實。為此,誤解就登上了星座,登上了宇宙,登上了萬有引力的高度。實際上,有一天他看到艾烏塞比奧因為病痛瀕臨死亡時,突然有了將女兒嫁給他的想法。假如那時候把丫頭嫁給那個垂死的瘋子,倒是很理想的事,因為既能避免現實中的諸多麻煩,又可以保留出嫁的全部價值。老早以前,馬努埃麗塔就長著一張寡婦臉。這位復闢派常常在夢中叫道:“我的小寡婦啊……”聽見這句話的人猜不出,這是指馬努埃麗塔?女英雄?泛指的女人?艾烏塞比奧?祖國?還是他自己? ……
譯者序言
翻譯了幾部阿根廷當代作家塞薩爾·艾拉的小說,閱讀了一些關於他的生平、創作經歷、作品評論和分析的西班牙語資料,感覺有些想法應該提供給我們的讀者,希望能夠幫助中文讀者理解他的創作指導思想、藝術手法和題材的選取。
1949年,塞薩爾·艾拉出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南部的普林格萊斯上校鎮。父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更是個狂熱的庇隆主義者,堅決支持庇隆總統的獨裁統治,是個參加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艾拉從小就對父親的不關心家務表示不滿,隻能依賴母親的呵護。他是獨生子,母親對他百般寵愛,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變得不愛說話,隻喜歡讀書。由於家離首都不遠,他經常在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閱讀各類書籍,對文學、歷史、哲學、音樂、美術等人文科學類的圖書都有廣泛涉獵,他雄心勃勃,想要當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進入青年時期,在大學裡,他廣泛接觸了歐美先鋒派文學和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其中阿根廷文壇上的博爾赫斯、羅貝托·阿爾特和曼努埃爾·普伊格,法裔美籍藝術家馬塞爾·杜尚、對超現實主義有重要影響的雷蒙·魯塞爾以及美國先鋒派音樂家、藝術家、哲學家約翰·凱奇對他後來的創作都有重大影響。
先鋒派文學的本質特征是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和欣賞習慣,主張獨c性、反叛性、不可重復性等原則。先鋒作家創造了新小說的概念、敘述方法和新的話語規範,尤其是對語法規則和邏輯性進行“顛覆”和“解構”。在思想內容方面,先鋒派作家講究直面人生,追求片面的深刻性,探求當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現作者的覺醒意識和身處邊緣的孤獨感。這在20世紀70到80年代的艾拉作品中多有印跡,其中馬塞爾·杜尚的“觀念藝術”理論對艾拉的影響尤其明顯。杜尚認為,藝術品的本質在於藝術家的思想,觀念是藝術的主體,文字、攝影、文件、表格、地圖、電影和錄影帶,加上觀眾的心智參與,都是觀念的表現形式。他還堅持認為,藝術價值在於“創意”(ideacreativa),而不在於展出的物品是否具有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瓷質的小便池上貼了一個“泉”字,送到展覽會上要求展出,被組委會憤怒地拒絕了。他們不懂得“泉”字背後的“創意”所在,這個字卻改變了人們通常的審美視角。杜尚的“觀念藝術”是反理性的,是反對傳統審美觀念的。他尖酸刻薄地質問:外在美是真美嗎?這讓我們聯想到,安徒生童話中皇帝的“新衣”是真的新衣嗎?杜尚極端的批判精神摧毀了種種傳統的藝術觀念,為新藝術流派的誕生解除了精神枷鎖。艾拉的文學創作深受他的影響。
在阿根廷國內,對艾拉影響最d的人物當屬博爾赫斯。這位阿根廷文學大師的寫作特點很多,讓艾拉直接受益的有:博爾赫斯打破了小說、散文、詩歌三者之間的界限;他的散文像小說,小說是詩歌,詩歌像散文。溝通三者的橋梁是作者淵博的知識和睿智的思想,是有創意的“點子”。三位一體,獨一無二,旨在表現“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例如短篇小說《阿萊夫》中就彙集了諸多主題:夢幻、迷宮、圖書館、虛構的作家、作品、宗教信仰、神隻等題目,有故事,有哲理,有散文詩素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渾然天成。在類似《阿萊夫》這樣的小說中,作者采用了時間和空間的輪回與停頓、夢境和現實的轉換、幻想和真實之間的界限自然連同、死亡和生命共時、像征和符號之間神秘的暗示等手法,把歷史、現實、文學、哲學(尤其是不可知論和神秘的宿命論)之間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們之間的疆界,創造出一個神秘、夢幻的虛構世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找到一條可以穿梭往來的通道,讓讀者獲得神奇的閱讀感受。
20世紀80年代末,歐美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延續和發展了先鋒派的衝擊力。從艾拉90年代的創作來看,他的確接受了後現代主義思想中的某些觀點,例如堅持反傳統的精神,堅持文學創作的不確定性,堅持寫作手法的多樣性和語言上的試驗,講究作品形式的光怪陸離,進一步打破真實和虛構之間的界限,消除陽春白雪和下裡巴人的邊界,追求作品主體的零散化和故事情節的碎片化。
從1975年到2017年間,艾拉創作了八十多部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這是一位高產作家。如果從創作題材上分類,70年代到整個80年代,艾拉的創作題材主要取自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風土人情,90年代的題材是“我”,2000年至今的主要題材是“藝術”。
大草原題材的主要代表是發表於1981年,也是艾拉成名作的《女俘愛瑪》。從選材的角度來說,《女俘愛瑪》與19世紀阿根廷浪漫主義文學大師埃斯特萬·埃切維裡亞的長詩《女俘》是唱反調的,是反傳統的“女俘”形像的。長詩《女俘》的主人公是個被凌辱、被欺壓、被傷害的女性,而艾拉筆下的女俘卻是個在困境中努力奮鬥的女子。她克服了種種生活中的困難,與軍人友好共處,善待印第安人,與要塞的上校結為好友,贏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終成功地創辦了一個養雞場。作者塑造了一個在逆境中勵志創業的模範典型。艾拉在另外一部小說《野兔》裡,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衝突處理成了“家族大團圓”,把大草原描寫成美麗、富饒、適合人類居住的樂園。這些看法與19世紀的大作家、阿根廷總統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對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薩米恩托在他的巨著《文明與野蠻》中提出:印第安人是“野蠻因素”,阻撓了社會進步和國內的經濟發展。艾拉不贊成這種看法,認為印第安人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是個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繫,應該向他們學習。
進入90年代,艾拉的創作題材轉向“我”,也就是“我”成為塑造的對像。“我”在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中處於中心地位。艾拉用自傳的內容和形式來表現小說故事的真實性,但是其中有很多虛構成分,實際上是真實與虛構的對立統一,真真假假,難以分辨。但是,作品的基礎仍然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彈子遊戲》和《晚餐》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兩部小說的主要情節都是“我”的切身經歷,前者是“我”去華人超市購物發生的故事,後者是“我”與一位脾氣怪異的朋友共進晚餐的故事。作品中發生的怪人怪事顯然都是虛構的,但是與真實的場景融會在一起,產生了十分逼真的藝術效果。
而到了21世紀,艾拉的題材選取轉向了“藝術”,“藝術”成為他最重要的創作源泉之一。艾拉通過筆下的人物,對某樣藝術品做出判斷和評論,進而引申到對文學自身問題的關注。比如在《巴拉莫》(Varamo)中,作者讓人物出來發表意見,批評專業寫作現像,主張自由快速書寫,強調藝術的生命在於創新。艾拉的藝術追求是打破文學、美術、音樂、魔術、舞蹈等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文學家、畫家、作曲家、魔術師、舞蹈演員齊聚一堂,各抒己見,旨在打破森嚴壁壘,支持新藝術家即興發揮。
縱觀艾拉三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他十分在意寫作手法的藝術創新。不錯,他的確深受國內外文藝思潮的影響,但是,他更注重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原創構思講究“智慧”,寫作手法講究“新奇”,敘述話語講究“怪異”,整個故事情節安排要“碎片化”。艾拉的這些表現在阿根廷當代文學的大合唱中屬於“不和諧音”。尤其是他遵循前輩博爾赫斯的教導,追求文學創作的世界性傾向。比如他的《小和尚》和《一部中國小說》,把小說的舞臺搬到了韓國、中國、巴拿馬、委內瑞拉,甚至包括歐洲和非洲國家。艾拉上述表現的理論基礎是超現實主義。艾拉承認,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例如表現驚奇、怪異、矛盾、荒謬、夢幻……駕馭意像,改變日常生活的現實感覺等)對他的創作有直接影響。但這僅僅是“影響”,是早期創作的表現。到了2016年,評論家伊格納西奧·埃切維裡亞問他與先鋒派文學的關繫時,他回答說:“我沒有先鋒派的外殼,我更喜歡傳統小說。我刻意追求創作新東西,其實骨子裡,我喜歡老東西。如果有人非要說我是先鋒派作家,那隻能說明我喜歡寫一些荒唐、怪誕的故事,因為我不喜歡老東西裡的裝腔作勢,我要借助藝術手段打假。”他堅信文學高於其他藝術門類,因為文學有自己的秘訣,可以囊括別的藝術門類,反之則不可能。
最近十幾年,塞薩爾·艾拉的文學作品和文藝思想在歐美文壇日益受到重視。早在21世紀初,拉美著名作家、《2666》的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就說過:“艾拉是西語文壇上為數不多的最y秀的作家之一。”面對贊譽和批評,艾拉都處之泰然。2018年4月25日曾有記者問他:“您總是能從日常瑣事裡找到快樂嗎?”他回答說:“是的,這正是因為我的寫作理想就是每天都追求變化。快樂就在於此,就在於做些天天有新意、不同的事情。我不擔心將來某一天沒了發現新意的能力,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寫完一部作品之後的大腦空白期。但是,第二天我總會冒出新想法。從天而降的新主意,新點子。誰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也許是看書,也許是道聽途說產生的聯想。因此可以肯定,新東西總會有的。讓我產生聯想的主要來源是閱讀。我認為作家的營養來自我們自身的第二人格、來自讀書的秘密‘超人’。想法可能來自任何地方,電視節目啊,生活瑣事啊,隨便一次談話啊。但是,通過讀書可以看到別的方面,會刺激我們繼續寫下去。我非常感謝閱讀,因為它曾經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時候,我膽小又近視,隻好藏到書堆裡,天長日久成了習慣,結果成了寫書人,寫出書來,再讓別人藏進去。”
他還對記者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讀書的趣味也在逐漸改變。一開始,我喜歡讀兒童讀物,連環畫、動漫故事、歷險記、海盜傳奇都是我的最愛。我還記得十一二歲時閱讀的海盜傳奇,作者是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多達二十一卷。後來,到了十四五歲,我發現了真正的文藝圖書,講藝術的圖書,還發現了博爾赫斯的作品,從此看起書來就變得非常挑剔了。”記者請艾拉說一說對圖像小說的看法。他說:“我深入過圖像小說的世界。如今,我不喜歡新的圖像小說,可我兒子是畫家,專門為美國出版圖像小說的出版社工作。我問兒子為什麼總是畫僵尸還魂、外星人登陸、海盜搶劫、納粹入侵,這些東西分分合合,沒有新花樣,毫無創意可言。我兒子成了圖像小說的雇傭軍。有人建議,讓我兒子為我的作品畫漫畫,可是我不感興趣。我一批評兒子的東西沒有創意,他就說,您可以為我寫一個有創意的腳本啊。我不願意寫腳本,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寫作方式。”
記者問艾拉是否閱讀過《堂吉訶德》,他的回答引出了一段大學時的讀書經歷,也值得說給讀者聽一聽:“我曾多次閱讀《堂吉訶德》,真是眼花繚亂,那是在大學期間,可以說是《堂吉訶德》把我領進了學術研究的世界。我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文學繫念書,大學畢業時,一位非常賞識我的老師派我去語言文學研究所做關於《堂吉訶德》的研究,選定的研究題目是《論作為對話體小說的〈堂吉訶德〉》。我開始讀書,做筆記,可是後來不知怎麼回事,雖然有了工作,收入也不錯,卻總覺得自己在學術研究領域做不出什麼成果。經過努力,我或許可以成為優秀的研究員,成為一名文學史專家,但是我寧願選擇放棄學術研究,去書寫自己的作品。我也不適合教書,口纔不行。”
從上述這段話可以看出,艾拉個性很強,不願意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這樣的個性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更是如此: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絕對不做社會、道義方面的承諾。針對尼加拉瓜著名作家塞爾希奧·拉米雷斯強調的“面對社會現實不肯睜開眼睛的作家,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職業”的觀點,艾拉明確表態:“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安安靜靜地閉上眼睛,不認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職業。我不明白,為什麼文學家一定要對周圍的社會政治現實做出承諾呢?為什麼?為什麼呢?可能是為了拿到文學獎吧。國內有些朋友總是勸我,稍稍努力一下,爭取拿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稍稍努力一下’,就是要我開口談談人權,談談民主。我可不想說這個。我寧肯生活在像牙塔裡,跟自己的圖書、詩歌和藝術在一起。我認為我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對身邊發生的一切當然感興趣,但感興趣的方式非常普通。我生來如此,有些東西我就是不感興趣。很多人喜歡政治和足球,我不喜歡。我喜歡的東西,幾乎沒人喜歡,這不是我的過錯。喜歡和不喜歡,互相彌補而已。”艾拉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現在方方面面。在阿根廷,公民投票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艾拉卻不在乎;他也去投票站,但是投棄權票,因為他不相信候選人的口頭承諾。但是,在他熱愛的文學藝術領域,他卻是忠貞不渝的。年輕時他也很喜歡美術,但是開始寫作之後,他就下決心要寫出好作品來。他堅信寫作這個行當全靠時間和實踐,創作的道路隻能自己走,別人的建議隻是參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作方式,如果隻是按照別人的方式寫作,往往有害無益。他這樣說,是有他自己的理論基礎的。他說:“社會得以幸存,是因為有誤會。以文學為例,作家寫的東西,他心裡明明白白,到了讀者手裡卻產生了誤會,難以被人理解。文學的寶貴之處就在這裡,因為簡單的理解可能就是傳達一個信息(今天有雨,明天放晴),而文學遠遠超出了傳達信息的功能,這超出的部分就在作家的明明白白和讀者的誤會之間。我經常想到我自己就是個讀者,這個讀者身份讓我嚴格控制自己寫的東西。”
艾拉的作品日漸受到歐美各國評論界和讀書人的關注。墨西哥大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經預言:2020年艾拉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近幾年來,在入選諾貝爾文學獎的外圍名單中,艾拉的聲望也逐漸提升,阿根廷國內很多人也希望除球星梅西之外,再來一個文學明星。對此,艾拉的態度是:“對我來說,這毫無意義,一旦獲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學獎項,就會變成公眾人物,這可是個大麻煩,因為會失去眼下默默無聞的地位;那樣一來,如果出門騎自行車,就會有人指指點點……不不不,太可怕了。我還是盡量保持現在的狀態吧,我連電視都還沒上過呢。不是因為我犯了法或者干了壞事要隱姓埋名,而是我想繼續低調地做好事呀。”
“繼續做好事”包括寫散文。2017年11月19日,文學評論家霍爾赫·卡裡翁發表了《塞薩爾·艾拉:優秀的小說家還是傑出的散文家?》一文。他介紹說:
“塞薩爾·艾拉有一本散文集,其中有許多精彩段落,比如他說‘要寫出好文章,是可以學習的;但是,下決心寫作絕非易事,因為寫作拼的是生命’。這類關於寫作和藝術的看法收在他的散文集《各種思想的延續》中,多數文章都談及當代文藝問題。他堅決扞衛浸透作家每個細胞的純文學,態度絕對是浪漫主義的。我們很容易在艾拉身上看到後現代主義和新先鋒派文學的影子,但是他還有少見的浪漫主義的一面。他的散文的確反映出他是個浪漫主義作家,很像是墨西哥大作家、偉大詩人帕斯在《污泥的兒女們》中刻畫出的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延續者的形像。近年來,他的散文創作轉向論述他的創作經驗和小說敘事理論,集中收在《各種思想的延續》、《論當代藝術》和《論遁詞》中。”這篇文章的最後,作者得出如下結論:“艾拉的散文篇篇優秀,而小說則參差不齊,原因是小說是他創作的實驗室,有探索的性質,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具有隨機性。而他的散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反思創作經驗教訓的結果,針對性很強,篇篇打中靶心。因此,他的散文勝過小說。”看來還需要把他精彩的散文引進到我國來啊。最後,我從譯者的角度說三句話:一是要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二是理解艾拉,尊重艾拉;三是是否借鋻艾拉,應該根據每人的實際情況而定,何況借鋻終歸是借鋻,沒人能代替自己的雙腳走路。
趙德明
2018年6月25日於觀瀾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