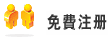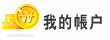第六章
馬來亞是我數次逃避中的第一次。
1951年,馬來亞上空籠罩著一片道德爭議的陰雲 – 到底有多嚴重,我到了印度後纔明白。對於英國人來說,戰爭背離正常,就像情感背離一樣。對於法國人來說,戰爭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愉悅的也可以是不愉悅的,就像通奸一樣。“La vie sportive(譯注:法語,意思是“體育的生活;運動的生活”等。)”– 這就是一位法國指揮官在西貢南部三角洲一艘小型登陸艇上對我描繪他的生活時說的話,他在一條條狹窄的水道裡追殺越盟(譯注:Viet Minh,1941-1951年間的抗日抗法組織越南獨立同盟會及其武裝部隊的非正式名稱。)遊擊隊,兩岸的迫擊炮火力很容易擊中他的小艇。
人說話要公正。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個地理問題。馬來亞比較靠近赤道;這裡幾乎每天下雨,因而總是霧氣蒙蒙;疲憊不堪、勞累過度的人們因此而更加精疲力竭,緊急法令時期所產生的工作鮮有人過問:管理勞工的人員太少,種植園主太少。除種屬於馬來亞公務員的種植園主和官員之外,這裡多數人干活都抱著臨時觀點:在他們的腦海裡,他們已經登上回家的小船。如果緊急法令時期結束(就像印度的法國人那樣,政府不正式稱之為戰爭),寬松政策就會較快出籠。但是,戰爭(名符其實地說,應該這樣稱它)毫無快要結束的跡像。與此同時,整個世界都在激烈爭論朝鮮戰爭是繼續還是結束,馬來亞那場被人遺忘的戰爭半死不活地拖著。每天零零星星都有人員死傷:1950年的前十一個月有四百平民慘遭殺害,一個遊擊隊營地被摧毀,三個遊擊隊員被槍殺,六人逃跑。戰爭就像迷霧:它滲透一切;它消耗精力;它含糊不清。它當然不是la vie sportive。
在馬來亞所有平民中,橡膠種植園主的處境最危險。共產黨突擊隊的打擊目標之一就是從經濟上毀壞這個國家,使它成為一個不值得維繫的地區,而馬來亞的財富主要是錫和橡膠。與橡膠園相比,錫礦相對比較容易守護,因此共產黨突擊隊的主要襲擊目標就是橡膠種植園主。那麼誰是橡膠種植園主呢?
去馬來亞之前我有一種想法,這種想法是從一份不同情的馬來亞狀況的報刊那裡偶然獲得的,這份報刊隸屬一幫資本主義大企業冷酷無情的,他們從不妥協,對當地勞工實行消極剝削,在當地俱樂部裡一杯接一杯地喝stengah(譯注:馬來語,意思是“一半”,但此處指一種用一半威士忌酒一半蘇打水再加冰塊合成的飲料。),也許還用薩默塞特?毛姆的方式,相互做愛。但是,在馬來亞居住不久,我了解到根本就沒有種植園主這回事 – 隻有X君或者Y君。
以X君為例。他與妻子生活在一棟兩層小樓裡,四周用帶刺的鐵絲網圍住;夜間,小樓周圍的場地用探照燈照亮,遠至第一排樹。他年紀五十多歲,曾經是日本人的囚徒,原本應該渴望比較輕松、比較富裕的晚年生活。他是個優秀的狩獵人,作為一名漁獵法執法官,原本應該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他的本職工作上(因為大像與共產黨一樣,必須與之鬥爭,他的種植園裡有一片特拉法爾加廣場大小的地方遭受大像蹂躪,就好像被炸彈炸過似的 – 沒有一棵樹木直立著)。
但是,他的餘生與他渴望的生活截然不同 – 如果有人能把這種沒完沒了的無法避免的暴力稱作生活的話。他沒有助手,因為幾個月前他的助手被謀殺在種植園裡,而他卻無法再雇傭一個……一天二十四小時,最靠近的村莊每隔半小時打一次電話過來,以確保電話線沒被割斷。有一次,他離開家宅僅一英裡便遭到伏擊,不過他開槍射擊殺出一條血路,還救出幾個受傷的同伴。在我來此暫住前不久,共產黨曾來過種植園,向園裡采集橡膠樹液的工人詢問他的動向(他的助手生前曾不明智地在固定的時間按固定的順序巡視種植園的幾片作業區)。當他到鐵絲網以外活動時(要是去幾百碼以外的種植園辦公室就好了),他手臂上掛著一支斯特恩式輕機槍(譯注:英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武器。),臀部別著一把自動手槍,皮帶上拴著兩個手榴彈。他是一個英勇無比、精力充沛的男子漢,既具有冒險精神又和藹可親,他不會考慮退休生活 – 他一生都在前線,他的前景不是安寧而是死亡,最近似安寧的生活就是偶爾去一次相對安全、官僚化了的首都吉隆坡。
如果早餐時他不喝咖啡而是喝一杯白蘭地和干姜水,那麼你幾乎不用驚訝。“酒後之勇,”他一邊對我說一邊按下防備不嚴實的小型裝甲汽車的起動按鈕,出發去巡視種植園,或者慢慢轉過死角,駛上通向村莊的道路,在這條路上,說不定哪一天,從對面叢林裡,斯特恩式輕機槍幾乎肯定會開火。在村裡,與中國店主一起喝一杯不加冰的啤酒;中國店主立場曖昧,店裡四周點著中國蠟燭,擺放著一箱箱茶葉;店主買下X君的廉價橡膠,充當他的錢莊(當場支付一)– 也許會把他的行動報告給遊擊隊。隨後,在軍官下榻的客棧裡喝上一兩杯紅杜松子酒,之後,便駕車沿著孤寂的兩英裡長的道路回種植園,在那片叢林圍牆前面的拐彎處放慢車速,十秒鐘神經極度緊張,隨後是橡膠園不堪一擊的防衛體繫,在那裡,死亡照樣可能發生,但是在那裡你至少能夠看清子彈來自單調的灰色軍服之間。一天早晨,我和他晚一個小時回家,他的妻子既生氣又愛憐,焦急等候著汽車的引擎聲響,直至他安全回到鐵絲網圍牆裡邊。那天晚上,廣播裡報道又有三個種植園主遭到謀殺。
或者以B君為例。他是另一位平民,在緊急法令情況下干著他和平時期的工作。他不是種植園主,而是一條重要鐵路樞紐的交通主管,在這裡,東海岸鐵路與吉隆坡-新加坡鐵路相銜接:他是個熊腰虎背的男子漢,讀書的品味讓人意想不到,在人際關繫方面相當敏感(他的所有助手都是印度人),我從未見過如此完美無缺的耐心。他的外貌像個軍士長,但行為卻像個醫生。
東海岸鐵路終止於彭亨州(譯注:Panhang,馬來西亞馬來亞地區州名。)。日本人毀壞了這條鐵路的延伸段,而B君管轄的這一段鐵路正在重新鋪設 – 他們對此事的感情相當復雜,因為要維持現存鐵路的安全運行已經不可能了。南新加坡線路上的夜間郵政列車已經完全放棄;東海岸鐵路線上,八臺機車已經無法正常使用,我不知道還有多少貨車不能正常使用。一年之中,整個鐵路繫統發生了四十九起火車脫軌事故。至於種植園主中的傷亡人數,傷亡率這麼高,多數軍隊覺得很難維繫他們的士氣。每節車廂裡的鐵路告示用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和中文表達:
告示:恐怖主義
一旦鐵路兩側發生交火
建議旅客們趴在車廂地板上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離開火車
一月份,我與B君一起在火車上度過好幾天。他的住宅前面一百碼開外就是無法避開的叢林;帶刺的鐵絲網、警察哨位、一種受約束的感覺。隨後,雨季來臨,二十五年來降雨量。因此,除強盜土匪外,又增添了洪水、衝潰、塌方等問題。人們會有一種老天不公的感覺,就像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在自己的民防區內發生一起嚴重事故時的感覺,另外,就是持續不斷,沒完沒了。人們覺得上帝應當每次隻給每人制造一個麻煩。
下面是“兩個盟軍”– 共產黨和自然災害 – 兩天的作孽時間表。自然災害打頭陣:
星期五,上午十點。新加坡方向的南線鐵路發生一起塌方。不過,發自吉隆坡的早班郵政車剛好已經通過,所以自然災害不得不再次采取行動。下午兩點。南線又發生兩起塌方。這時,救險火車載著一隊士兵出發,試圖去清理鐵道,為第二天早晨的火車開闢道路。
整個晚上,我能聽見電話鈴不時作響 – 這使我想起種植園主的住宅。星期六凌晨一點,發電廠遭水淹,於是就停電。凌晨兩點一刻,共產黨走出叢林,使救險火車出軌。凌晨四點,通往鐵路樞紐的陸路完全被切斷,東海岸鐵路被洪水衝斷。早餐時刻,供水中斷 – 在傾盆大雨中,這可是一樁令人不爽的怪事。甚至四分之一英裡外的車站也必須靠蹚水抵達。北邊又發生一起塌方事故。
傍晚,我們蹚水前往車站,借著燭光坐在小喫部裡,與此同時,各種信息紛至沓來。甚至鐵路信號匣也隻能用油燈昏暗照明;人影消失在長長月臺的黑暗之中,整個朦矓的車站和它潮濕的場地有一種奇怪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氣息,仿佛電還沒有運用。傍晚六點,南邊發生一起衝潰,北邊又發生一起塌方。晚上八點三刻,一列東海岸列車脫軌 – 這次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共產黨干的。必須動員小鎮上所有的勞力,借著油燈的光亮,給貨車車廂裝載道砟,但是有足夠的勞力,足夠的道砟,足夠的貨車車廂嗎?這位個子高大耐心十足的男子漢不時放輕腳步走回到他的酒杯跟前,對著雨天、寒冷和敵人放聲大笑,平靜地等待下一份災難電報。人們常常談起士兵與平民,但是沒有比B君更好的士兵了。這場戰役與在叢林中跋涉搜尋一樣非常危險,他的軍隊遭到洪水以及突擊隊的埋伏,他像一個優秀的指揮官一樣,得到部下的愛戴。因此,我在吉隆坡經常發現自己在思考:如果政府官員像這些人 – X君和B君 – 那樣工作該有多好!不過,在沒有危險的地方,你也許找不到勇氣,而且愛戴也許也是戰時的產物。
這場戰爭的性質國外幾乎無人明白。它不是一場民族主義戰爭;參戰人員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國人,在叢林中參戰的少量馬來亞人中,較大一部分人是印度尼西亞恐怖分子。我訪問過吉蘭丹州(譯注:Kelantan,馬來西亞馬來亞地區州名。),在這個州裡,馬來亞人占絕大多數,去那裡就像到訪異國他鄉。這裡平靜安寧:你可以不帶武器隨意走動;公路上不需要護送車隊;四周有一種幸福美滿的氣氛;人們的服飾比較艷麗;甚至太陽也似乎更加燦爛,因為叢林幾乎已經漸漸遠去。我已經多麼厭倦那片昏暗敵意的綠色圍牆:叢林不再是中立的了!
我們英國人的良知可以很清晰 – 我們不會在違背馬來亞人意願的情況下強行控制他們;我們與他們一起以及共產主義的中國追隨者,這是一場更加重大的戰爭,遠不止報界使用“土匪”一詞的含義。土匪不可能像這些人那樣年復一年在艱苦的叢林中幸存下來:幾千名土匪不可能堅持與幾十萬武裝馬來亞警察、兩萬五千名英國、廓爾喀(譯注:Gurkha,西方國家對尼泊爾人的統稱。)和馬來亞軍隊作戰。這些人是共產主義突擊隊,按俄國師的編制組建,有他們的政治機構,他們的教育機構,他們的政治委員,他們不知疲倦勤奮努力的情報機構。沒人知道他們的總司令部在那裡 – 也許在某個城市裡,新加坡,吉隆坡,甚至在古老、相對安寧的馬六甲城 – 但是,它的領導人卻是路人皆知的。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本人英勇戰鬥,曾行進在倫敦勝利大遊行的隊伍之中。
你必須在馬來亞叢林中至少生活過幾天纔能理解它的艱難困苦和單調乏味。它比緬甸的叢林稠密得多,它妨礙行動,在叢林中一小時還走不到一英裡。林中的能見度有時隻有二十英尺。幾乎每天大雨如注灌澆叢林,這使得無數山崗陡峭溜滑的山坡極難攀登。人們的身上沒有一刻是干燥的,夜晚也沒有一刻是安寧的 – 各種昆蟲難聽嘈雜的叫聲不時打擾著初到乍來者和他的美夢。行軍時暫時停下歇一歇,你就能看見許多螞蝗朝你的靴子爬去 – 細火柴杆似的蟲子,伸屈著身子在一片片潮濕的葉子上盲目地蠕動,稍後如果在你的衣服上找到開口處,它們就會膨脹成一條條肥肥的灰色鼻涕蟲。還有那種永遠不會散去的叢林惡臭 – 腐爛植物發出的濃重氣味。這種氣味會黏在你的衣服上久久不散。當你走出叢林時,你的朋友們會躲避你,直至你沐浴更衣。
在馬來亞作戰的英國部隊很多 – 皇家燧發槍團、皇家海軍陸戰隊、伍斯特郡軍團、奧爾巴尼公爵團,僅舉幾個為例 – 如果列舉我所在的廓爾喀步槍團為例,那隻是因為他們非常好客,允許我隨他們一起在彭亨州進行一次最小規模的作戰行動。然而,敵人的確區分廓爾喀步槍團和它的其他對手。一份繳獲的情報顯示,敵人相當不公正地鄙視馬來亞團,說英國軍隊非常勇敢,但非常喧鬧 – 很遠就能聽見英國軍隊來了 – 不過,廓爾喀步槍團非常兇猛而且非常安靜。
廓爾喀步槍團是一支雇傭軍。這支部隊的職業就是消滅它正式的敵人,也許因為它有一份真正的職業,所以它特別馴服。廓爾喀步槍團沒有女人的麻煩 – 他們把一種妻子兒女的幸福家庭生活隨軍帶到駐地。廓爾喀士兵領取薪酬,作為回報,他們對英國軍官絕對忠誠,他們的長官報以愛兵如子,這在其他任何部隊都是沒有的。英國兵團的軍官們抱怨說,他們在廓爾喀步槍團的同事們喋喋不休地談論他們的士兵,他們的士兵是他們的激情。
廓爾喀巡邏兵行動靠羅盤不靠道路。他們按直線運動。皇家空軍轟炸了某個地區,據悉二百名共產黨突擊隊員在那些特殊地圖方塊內的某個地方來回亂竄。一個由十四名士兵組成的廓爾喀排在一名英國軍官的帶領下,被認為足以完成偵察任務。巡邏隊從營地直徑出發,穿過炊事區,穿過狹窄的橡膠林區,進入熱帶密林。我們的目的地是這片叢林另一邊的主干道,離開我們僅九英裡,但是我們走了兩天半,過了兩夜纔到達那裡。我們出發比較晚,五小時行軍後,我們就開始宿營。當確定我們方位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叢林中穿行了三英裡多。面前是重重疊疊漫無盡頭的五百英尺高的山崗,溜滑的紅土山坡幾乎成四十五度斜角。廓爾喀士兵即便試圖借助樹枝攀登,但有時也難免滑倒,他們叢林靴的橡膠鞋底在爛泥和樹葉黏液裡無法支撐。
經驗證明這種靠羅盤走陡峭山間小路的方法是正確的。如果像英國軍隊那樣沿著小路巡邏,你可以避開最難攀登的山崗(在這一地區,山崗有時高達兩千英尺),也永遠不必在灌木叢中披荊斬棘開闢道路,但是,當你在巡邏的那一條小路上尋找敵人蹤跡時,你是在拿全體將士的性命冒險。廓爾喀兵團的戰術意味著,在一天時間之內,在尋找敵人蹤跡的時候,你穿越了許多條小路;一根剛折斷的竹子,竹液還是濕的,這也許是的敵情。
四點半停止行軍,給部隊時間在天黑以前安營扎寨。首先選好幾處哨位,然後用kukris(譯注:印度廓爾喀人用的闊頭彎刀。)(那種神奇的多用途武器)砍伐樹枝,每兩人搭建一間棚屋,一張鋪地防濕布撐開遮在棚頂上,以防夜間下雨;另一張防濕布鋪在用樹枝和樹葉建成的臥床上;在用砍刀開闢出一片空地架設無線電收發機,收發機的天線被投擲到一百英尺的高處。夜幕開始降臨,這時kukri成了開罐器。在一隻大約9 x 4 x 3英寸的罐頭裡裝著廓爾喀士兵們的口糧 – 米飯、葡萄干、咖喱粉、茶葉、糖以及一盞小酒精燈和固體燃料,用以烹調。黑夜中,那一盞盞酒精燈微弱的火焰就像保育院裡的夜明燈。我的同伴奇爾斯少校直挺著身子傾聽,但不是在聽共產黨的動靜。他低聲說,“我總在傾聽一種鳥 – 黃昏和黎明都在聽。聽,那聲音就是!像鈴聲。你聽見了嗎?”除了叢林營地的噪雜聲,我啥也沒聽見。早晨六點,少校站在我們臥床邊夜間暴雨造成的新泥漿裡。“就在那裡!你聽見了嗎?”他低聲說。“像鈴聲!”
經過一天半強行軍和艱難攀爬,除發現兩處被遺棄的營地外,一無所得。我們在離開出發地九英裡的地方走出叢林 – 在作戰指揮室的地圖上可以添上兩個紐扣,僅此而已;除一枚空炮彈殼外,甚至沒有空襲的跡像,還有一處塌方,那也許是大雨造成的;例行的巡邏,常見的螞蝗,常遇的疲勞,還有常聞的惡臭。
不過,我們可以沐浴和更衣,而共產黨軍隊始終生活在他們潮濕的綠色樊籠裡。
因此,為了提振士氣,他們講課,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用膠版謄寫機印刷《列寧新聞》和《紅星報》,召開自我批評會。與不知悔改的恐怖主義相比,顯得多麼奇特幼稚!人們可以用繳獲的文件勾畫出這種生活的景像:人們獲悉李慶“不太衛生”,阿蔡“具有友善的團隊精神”,劉奔有點懶惰,學習拖沓,“行為不太討人喜歡”(他有時“擔心形勢”,他的同志們認為他“相當不成熟”)。
對待愛情,他們既嚴格又同情(叢林軍隊中有許多婦女)。從繳獲的《列寧新聞》中,人們了解到未婚男女同志禁止獃在一起,除非獲得高一級長官的特準。“我們不禁止任何人做愛。但是,這種性愛必須是符合規定的。一旦愛情確立,當事人應該向組織報告此事和確切情況。此事必須經過組織調查,然後根據組織決定通知雙方。”下面是事先確定的討論題:
1. 共產黨人的愛情為什麼是一種嚴肅的本能?
2. 什麼是正確的愛情觀?
3. 目前我們這個地區是否還存在少數幾種不正確的戀愛觀?
4. 它們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的?
5. 原因是什麼?
6. 我們對待愛情的態度是什麼?
7. 我們如何克服不正確的戀愛觀?如何對待不正確的愛情?
想到這些問題是用漂亮的正楷從右到左的倒著書寫出來,人們心中就會感到非常奇怪,在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看來,自從兩千多年前詩人枚乘用毛筆作詩以來,這種書法幾乎沒有變化,下面是枚乘寫的愛情詩(埃茲拉?龐德[譯注:Ezra 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翻譯家。]譯):
青青河畔草,
郁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窗牗。
纖纖出素手……
人們一想到這場緩慢耗時令人生厭的馬來亞衝突,就會想起這首詩歌,多麼不可思議的對比!有位巡邏兵發現了一個孤身一人的遊擊隊員,他顯然沉浸在一種文學練習之中 – 他必須從用膠版謄寫機印刷的一些句子中發現並糾正錯誤。一個種植園主與他的妻子駕車前往吉隆坡俱樂部出席一次蘇格蘭晚宴,晚宴菜單是“蘇格蘭肉湯、迪河鮭魚、羊肉雜碎布丁、土豆泥、碎蘿卜、迪內高地特色菜、糖豌豆、烤土豆、巴爾莫勒爾聖代。”當消息傳來他們兩歲的女兒被華人分子近距離平射致死時,他們不是剛好在喫羊肉雜碎布丁那道菜嗎?“黨解決了愛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