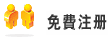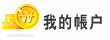自序
一
我辭去院長職務之後,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襖,獨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間整整十年,去尋找中華文化的關鍵性遺址。
當時交通還極其不便,這條路走得非常辛苦。總是一個人背著背包步行,好不容易見到一個鄉民就上前問路,卻怎麼也問不清楚。那年月,中國各地民眾剛剛開始要去擺脫數百年貧困,誰也沒有心思去想,在數百年貧困背後是否還蘊藏著數千年魂魄。
終於,我走下來了,還寫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與廣大讀者一起,梳理了中華文化的經絡。
接下來的問題無法回避:這樣一種悠久的文化,與人類的其他文化相比處於什麼地位?長處在哪裡?短處又在哪裡?
在尋訪中華文化遺址的十年間,我也曾反復想過這些問題,還讀過不少對比性的文獻。但是,我隻相信實地考察,隻相信文化現場,隻相信廢墟遺跡,隻相信親自到達。我已經染上了盧梭同樣的毛病:“我隻能行走,不行走時就無法思考。”我知道這種“隻能”太狹隘了,但已經無法擺脫。對於一切未經實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結論,本不應該全然排斥,但我卻很難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進到了一個尷尬境地:要麼今後隻敢小聲講述中國文化,要麼為了能夠大聲,不顧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重要的廢墟。
我知道,後一種可能等於零。即便是人類歷史上那幾個著名的歷險家,每次行走都有具體的專業目的,考察的範圍也沒有那麼完整。怎麼能夠設想,先由一個中國學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
但是,恰恰在不可能的地方出現了可能。就在二十世紀臨近結束的時候,天意垂顧中國,香港鳳凰衛視突然立下宏願,要在全球觀眾面前行走數萬公裡,考察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址,聘請我擔任嘉賓主持。聘請我的理由,就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文化,呈現出了自身的伸展邏輯。
二
這個行程,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義蔓延的地區,例如北非、中東、南亞,而且還必須貼地穿越。對此,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一個集團能作出安全的保證,包括美國和歐洲的幾個發達國家在內。所以,多少年了,找不到有哪個國家派出過什麼采訪組做過類似的事,更不必說采訪組裡還躲著一個年紀不輕的學者。
感謝鳳凰衛視為中國人搶得了獨占鼇頭的勇敢。但是,對於一路上會遇到什麼,他們也沒有把握。王紀言臺長壓根兒不相信我能夠走完全程,不斷地設想著我在沙漠邊的哪個國家病倒了,送進當地醫院,立即搶救,再通知我妻子趕去探視等等各種預案。他們還一再詢問,對於這樣一次兇吉未卜的行程,需要向我支付多少報酬。我說,這本是我夢想中的考察計劃,應該由我來支付纔對。
我把打算參加這次數萬公裡歷險的決定,通知了妻子。我和妻子,心心相印,對任何重大問題都不必討論,隻須通知。但這次她破例說,讓她仔細想一想。妻子熟知國際政治和世界地圖,這一點與其他表演藝術家很不一樣。那一夜,她滿腦子都是戰壕、鐵絲網、地雷、炸彈。終於,她同意了,但希望在那些危險地段,由她陪著我。
臨出發前,我和妻子一起,去與爸爸、媽媽告別,卻又不能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們。不是怕他們阻止,而是怕他們擔心。尤其是爸爸,如果知道我的去向,今後的時日,就會每天深埋在國際新聞的字裡行間,出不來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年邁的媽媽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神色詭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說要送給她一個特殊的禮物。這個禮物,就是我剛出生時穿的一雙鞋。妻子一下子跳了起來,兩手捧起那雙軟軟的小鞋子,低頭問她:“媽媽,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那雙肉團團的小腳,將會走遍全中國,走遍全世界?”
三
整個行程,是一個偉大的課程。
面對稀世的偉大,我隻能竭力使自己平靜,慢慢品咂。但是,當偉大牽連出越來越多的兇險,平靜也就漸漸被驚懼所替代。
吉普車貼著地面一公裡、一公裡地碾過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裡會遇到什麼。我是這伙人裡年齡大的兄長,大家要從我的眼神裡讀取信心。我朝大家微微一笑,輕輕點頭,然後,繼續走向前方。前方的信息越來越喫緊:這裡,恐怖主義分子在幾分鐘內射殺了幾十名外國旅客;那裡,近兩個月就有三批外國人質被綁架;再往前,三十幾名警察剛剛被販毒集團殺害……
我這個人,越到艱難的時刻越會迸發出大的勇氣,這大概是兒時在家鄉虎狼山嶺間獨自夜行練下的“幼功”。此刻我面對著路邊接連不斷的頹壁殘堡、幢幢黑影,對伙伴們說:“我們不裝備武器,就像不戴頭盔和手套,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撫摸一個個老人身上的累累傷痕。”
如此一路潛行,我來不及細看,更來不及細想,隻能每天記一篇日記,通過衛星通訊發送到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讓廣大讀者一起來體會。但在這樣的險路之上,連記日記也非常困難。很多地方根本無法寫作,我隻能趴在車上寫,蹲在路邊寫。漸漸也寫了不少,我一張張地放在一個洗衣袋裡,積成了厚厚一包。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這一目前世界上危險地段時,我把這包日記放在離身體近的背包裡,又不時地把背包拉到身前,用雙手抱著。晚上做夢,一次次都是抱著這個背包奔逃的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結果都一樣:雪花般的紙頁在荒山間片片飄落,匪徒們紛紛去搶,搶到了拿起來一看,卻完全不認識黑森森的中國字,於是又向我追來……
四
這雪花般的紙頁,終於變成了眼前的這本書。
從紐約發生“9?11事件”後的第二天開始,我不斷收到海內外很多讀者的來信、來電,肯定這本書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恐怖地區的所在,並憂心忡忡地發出了警告。韓國和日本快速地翻譯了這本顯然太厚的書,並把這件事說成是“亞洲人自己的發現”。
不久,聯合國舉辦的世界文明大會邀請我向世界各國代表,講述那再也難以重復的數萬公裡。但是,我在演講的開頭就聲明,我自己看重的,不是發現了那數萬公裡,而是從那數萬公裡重新發現了中國文化。
熟悉我文風的讀者,也許會抱怨這本書的寫法過於質樸,完全不講究文采,那就請原諒了。執筆的當時完全沒有可能進行潤飾和修改,過後我又對這種特殊的“寫作狀態”分外珍惜,舍不得多加改動。我想,匆促本是為文之忌,但是,如果這種匆促出自於一種萬裡恐怖中的生命重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現在這個版本與原來的版本有較大不同的地方,是後部分。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後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尼泊爾博克拉一個叫“魚尾山屋”的旅館中,對一路感受的整理。當時在火爐旁、燭光下寫了不少,而每天要在各報連載的隻是其中一部分。這次找出存稿,經過對比,對於已經發表的文字有所補充和替代。
我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稍稍彌補了每天一邊趕路一邊寫作的匆促。讀者既然陪我走了驚心動魄的這一路,那麼,後也不妨在那個安靜的地方一起坐下來,聽我聊一會兒。世界屋脊下的爐火、燭光,實在太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