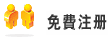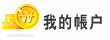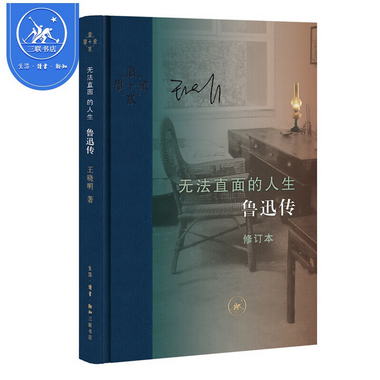
出版社:三聯書店 ISBN:9787108069245 商品編碼:10048637050403 開本:16開 出版時間:2021-01-01 代碼:43 作者:馮金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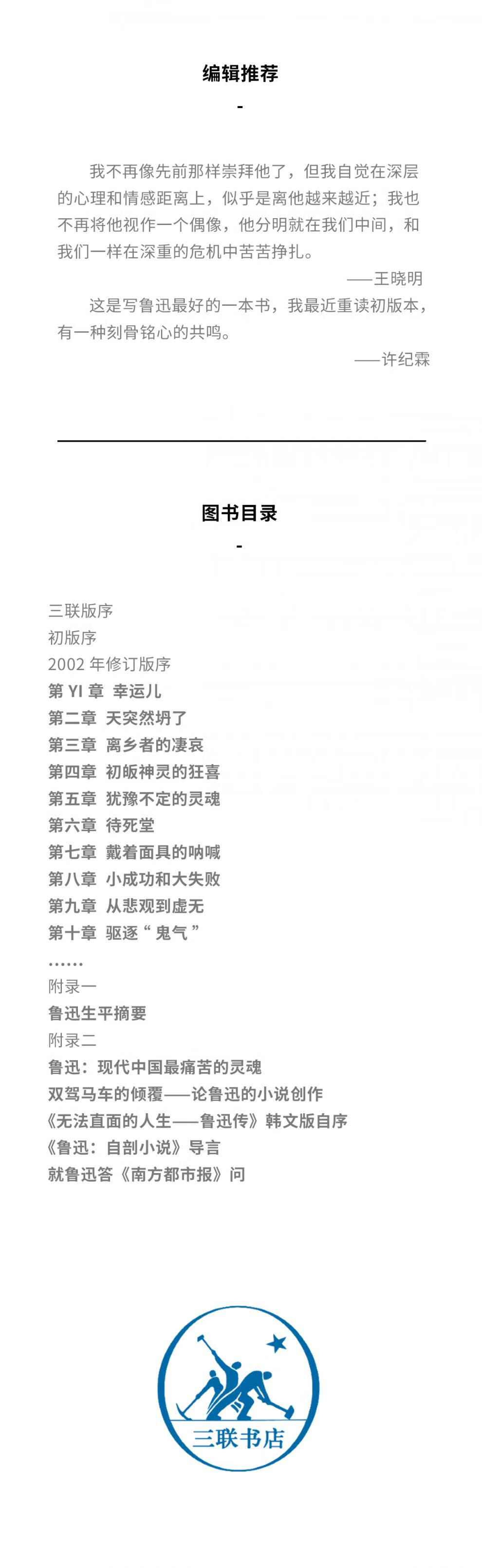   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王曉明
這是寫魯迅 的一本書,我最近重讀初版本,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共鳴。 ——許紀霖 

三聯版序 初版序 2002年修訂版序
章 ?幸運兒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第三章 ?離鄉者的淒哀 第四章 ?初皈神靈的狂喜 第五章 ?猶豫不定的靈魂 第六章 ?待死堂 第七章 ?戴著面具的吶喊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失敗 第九章 ?從悲觀到虛無 第十章 ?驅逐“鬼氣” 第十一章 ?魏連的雄辯 第十二章 ?女人、愛情和“青春” 第十三章 ?沒完沒了的“華蓋運”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喪 第十五章 ?一腳踩進了漩渦 第十六章 ?新姿態 第十七章 ?“還是一個破落戶” 第十八章 ?“橫站” 第十九章 ?《死》 第二十章 ?“絕望的抗戰”
附錄一 魯迅生平摘要 附錄二 魯迅: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 雙駕馬車的傾覆——論魯迅的小說創作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韓文版自序 《魯迅:自剖小說》導言 就魯迅答《南方都市報》問 

當然,在和“鬼氣”的對抗中,魯迅並非處處失敗。自從回國以後,他就不再是一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他賴以對抗“鬼氣”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種明確的理想主義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發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罷,想告別魏連殳也罷,都主要是這本能勃發的結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掙不脫“鬼氣”的包圍,他也會在其他方面繼續掙扎。到1925年,他終於在一個方向上打開了缺口,那就是對女人的愛情。?
我們都還記得,一直到1920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說是毫無女性的溫馨氣息的。為了不使母親傷心,也為了維持自己的名譽,他甘願過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雖說自己願意,這樣的日子卻非常難捱,1918年初,他的一位生性灑脫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嘆:“家叔曠達,自由行動數十年而逝,僕殊羨其福氣”,?就透漏出他對自己這狀態的不滿有多麼深切。隨著對民族和社會的失望日益加深,又與周作人鬧翻,大家庭的理想破滅,內心深處的虛無感彌漫開來,他這不滿也一天比一天壯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犧牲的無謂,不想再那樣“認真”麼?他不是說從此要顧自己過活,隨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別人耕地麼?原先重重地壓在背上的那些責任感,似乎日益顯出它們的輕薄,他勢 一次次反問自己:你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不就是衝出單人禁閉的囚室,尋一位真心喜愛的女人嗎?他在虛無感中陷得越深,那孝道和婚姻的束縛力就越減弱,我簡直想說,正是那“個人主義”的情緒,激活了他追求愛情和個人幸福的激情。 他開始和姑娘們來往,有的來往還相當密切。到女子師範大學任教之後,他的客廳裡更出現了一群聰明活潑的女大學生。有一次過端午節,他請她們來家中喫飯,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顴骨”,又“案小鬼[指許廣平]之頭”,?手舞足蹈,開懷大樂,那久受壓抑的生命活力,勃然顯現。?
就這樣,在1925年夏天,魯迅和這群女學生中的一個——許廣平——相愛了。 (此處空一行)
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比魯迅年輕近20歲。雖是南方人,身材卻頗高,好像比魯迅還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卻是那群女學生中最有纔華的一個 ,對社會運動,甚至對政治運動,都滿懷熱情。她敬仰魯迅,也能理解他,對他的追求就更為熱烈。你不難想像,當她表白了愛情,又從他那裡收獲同樣的表白的時候,她的心情會多麼興奮。?
但是,魯迅的心情卻復雜得多。他愛許廣平,但對這愛情的後果,心中卻有疑慮。這疑慮還是來自虛無感,它就像一枝鋒利的雙刃劍,既戳破孝道之類舊倫理的神聖性,又戳破個性解放、“愛情”之類新道德的神聖性,它固然鏽蝕了魯迅的精神舊宅的門鎖,卻也會當著他的面,把他打算遷去的其他新居都塗得一團黑。傳統的大家族當然是無價值的,孝道也可以說是無謂的,但那新女性的豐采,戀愛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個幻像呢?魯迅早已過了“情人眼裡出西施”的年齡,再怎樣喜愛許廣平,也不會看不出她的缺陷。社會又那樣險惡,在1925年,無論北京的學界還是官場,都有一股對他的敵意在蜿蜒伸展,一旦他背棄自己的婚姻,會不會授那些怨敵以打擊的口實呢?倘若種種打擊紛至沓來,他們的愛情禁受得住嗎?在寫於這時候的短篇小說《傷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繪得那麼絕望,把他們承受不住社會壓力、愛情逐漸變質的過程表現得那麼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慮有多深,思緒怎樣地偏於悲觀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動非常謹慎。他向許廣平表明,他無意和她正式結婚,在名分上,他還保持原來的婚姻。這實際就是說,他並不準備徹底拆毀那舊式婚姻的囚室,他僅僅是自己鑿一個洞逃走。他也不想馬上和許廣平同居,固為條件還不具備,還需要作些準備。 首先是錢。為了購置磚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經欠了朋友800塊錢的債,一直無力償還;他又纔被章士釗革職不久,倘若因為與許廣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輸了官司,那豈不是要落入涓生式的惡運了嗎?其次,他也不願在北京與許廣平同居,離母親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畢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氣又日漸壓抑,後來更發生“3·18”慘案,搞得他幾次離家避難,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家庭,總得另尋一處安全的地方。 當然,他最擔心的,還是和許廣平的愛情本身。這裡既有對許廣平的疑慮,也有對自己的反省。“我已經是這個年紀,又有這麼多內心的傷痛,還能夠容納這樣的愛情,還配得上爭取這樣的愛情嗎?”“讓她這樣與我結合,她的犧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現在甘心情願,以後會不會後悔?”“她究竟愛我到了什麼程度?”…… 我相信,每當夜晚,他躺在床上抽煙默思的時候,類似上面這樣的疑慮,一定會在他心中久久盤旋,去而復返。他面前似乎已經浮出了一條逃離絕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時往裡走,又怎樣走進去,卻不容易下決斷。
1926年初春,一個新的機會來了,新任廈門大學國學繫主任的林語堂,是魯迅的老朋友,邀請他去廈門大學任教。那裡遠離北京 ,鄰近廣東,不但氣候溫暖,政治空氣也似乎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400塊錢的薪水,正是一個適合開始新生活的地方。魯迅欣然應允,就在這一年8月離京南下,適逢許廣平要回廣州,便一同動身。 但是,盡管有這麼合適的機會,又是與許廣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確的計劃。他隻是與許廣平約定,先分開兩年,各自埋頭苦干,既是做一點工作,也為積一點錢,然後再作見面的打算。?你看,他還是用的老辦法,當對將來缺乏把握、難下決斷的時候,就先將決斷往後推,拖延一陣子再說。 (此處空一行)
魯迅興致勃勃地踏上了廈門島。可是,幾乎從 天起,種種不如意的事情就接踵而來。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閉塞,學校主事人那樣勢利,教師中的淺陋之徒又這麼多,再加上若干職員和校役的褊狹懶散,終至使他連聲嘆息:自己還是天真了,民國首府的北京都那樣糟糕,廈門還會好麼? 他尤其惱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學者對頭——他稱之為“現代評論派”的,如今也紛紛南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廈門大學,和他做同事。譬如顧頡剛,他曾公開說佩服胡適和陳西滢,現在然也到廈門大學來做教授了;自己來了不算,還 其他的熟人來,這些被薦者來了之後,又引薦另外的人,這在魯迅看起來,簡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他寫信對許廣平抱怨:“‘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裡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遠遠地躲到廈門來,竟然還是會遇上他們;在北京受排擠,跑到這裡來還可能受排擠,這怎麼能不教他光火呢? 於是他這樣向朋友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觸,就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無人澆一杯冷水,於是終於決定曰:仰東碩殺!我勿要帶來者!”?“仰東碩殺”是紹興土話,意思是“操他媽的!”廈門大學竟然逼得魯迅不斷要在心裡罵出這樣的話,他當然不願在這裡久留了。到廈門不到4個月,他就開始想走。一個學期的課還沒講完,就已經向校方遞了辭呈。他原想在廈門大學工作兩年,現在卻提前一年半離開,當他獨自一個人在夜燈下寫辭呈的時候,先前的種種走投無路、屢屢踫壁的記憶,一定又會湧上腦際吧。
處在這種經常要罵出“仰東碩殺”的心境裡,他對與許廣平的愛情的疑慮,自然會逐漸加重。1926年11月,他寫信對她說: 常遲疑於此後所走的路:(一),積幾文錢,將來什麼都不做,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做一點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當然有時仍不免),倘同人排斥,為生存起見,我便不問什麼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多了,終於覺得太傻。前一條當先托庇於資本家,須熬。末一條則太險,也無把握(於生活)。所以實在難於下一決心,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
他是真的想不好:雖然列出了三條路,想走的卻是第三條;但他不知道許廣平是否真願意和他攜手共進,也不知道這條路是否真能夠走得通。疑慮重重之際,就干脆向許廣平和盤托出,既是試探,也是求援。?
許廣平是多麼敏感的人,立刻就覺出了魯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慮,也知道這疑慮的深廣,她甚至還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後退,這自然使她深為不滿,就用了這樣激動的口氣回信說: 你信本有三條路,叫我給“一條光”,我自己還是瞎馬亂撞,何從有光,而且我又未脫開環境,做局外旁觀。我還是世人,難免於不顧慮自己,難於措辭, 但也沒有法了。到這時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你疏遠的人,發一套批評,我將要說: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為舊社會犧牲。換句話,即為一個人犧牲了你自己。而這犧牲雖似自願,實不啻舊社會留給你的遺產。……你自身是反對遺產制的,不過覺得這份遺產如果拋棄了,就沒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遺產。……我們是人,天沒有叫我們專喫苦的權利,我們沒有必喫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們是人,天沒有硬派我們履險的權力,我們有坦途有正道為什麼不走,我們何苦因了舊社會而為一人犧牲幾個,或牽連至多數人,我們打破兩面委曲忍苦的態度,如果對於那一個人的生活能維持,對於自己的生活比較站得穩,不受別人借口攻擊,對於另一方,新的部分,兩方都不因此牽及生活,累及 立足點,則等於面面都不因此難題而失了生活,對於遺產拋棄,在舊人或批評不對,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無理批評,即批評也比較易立足。……因一點遺產而牽動到了管理人行動不得自由,這是在新的狀況下所不許,這是就正當解決講,如果覺得這批評也過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談話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沒有不能喫苦的。 這信寫得很動情,也許是急不擇言吧,許多話都說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魯迅不願意解除舊式婚姻的內心原因,又用那樣熱烈的口氣激勵他作出決斷。她甚至不隱瞞自己的焦急和不快, 那一段話,簡直是在賭氣了。?
幸虧是這樣的急不擇言,反而打消了魯迅的疑慮。說到底,他 的顧慮正在許廣平本人,現在從她的這封信,他看見了她的真心,許多擔心和猶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語氣非常誠懇,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態度也很樂觀。似乎是決意要走第三條路了: 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聽人安排,……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動的巨變而失力量。 ……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 ……離開此地之後,我 改變我的農奴生活,……我覺得現在H.M. [即“害馬”,對許廣平的昵稱] 比我有決斷得多…… 一個多月以後,他更明白表示:“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隻要梟蛇鬼怪夠了”,?這所謂“梟蛇鬼怪”,就是指許廣平。
正在他終於確信了許廣平的愛情的同時,廣州的中山大學接連來信,熱情地邀他去擔任國文繫的教授和主任。這無疑從另一面增強了他的勇氣。人世間不但真有值得信賴的愛情,他自己也還有可以闊步的生路,無論從哪一頭看,他的境況似乎都比涓生好得多,在爭取新生活的方向上,他確乎應該試一試了。 從事後的旁觀者的眼光看,這自然是又有點陷入錯覺了,但是,一個剛剛開始全身心浸入愛情的人,多半會情不自禁地把整個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會以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個新天地,魯迅的這一點錯覺又算得了什麼?他內心的虛無感是那麼深厚,他大概也隻有靠這樣的錯覺,纔能夠擺脫它的羈絆吧。 他終於下定了決心。1927年1月到廣州,住進中山大學之後,即由許廣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來訪,她也並不回避。10個月之後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雲裡租了一幢3層的房子,與許廣平公開同居。在舊式婚姻的囚室裡自我禁閉20年之後,他總算逃出來了。 (此處空一行)
身邊有了許廣平,魯迅似乎年輕了許多。他的衣著現在有人料理,頭發和胡須現在有人關心,在那麼長久地禁欲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了女性的溫暖和豐腴,他的整個心靈,都因此變得松弛了。在廣州,他與許廣平等人接連遊覽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電影,滿臉歡愉,興致勃勃。到上海之後不久,又和許廣平去杭州遊玩,雖然是七月份,暑熱逼人,他卻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陪同遊玩的許欽文和章廷謙都暗暗,從他們十幾年前做魯迅學生的時候起,還從未見他表現過這樣濃的遊興。 魯迅本是一個善感的人,你隻要讀過他的《社戲》,就一定會記得他對家鄉風物的那份善感的天性。可是,由於家道中落以後的種種刺激,到了青年時代,他卻對自然風景失去了興趣。他在東京那麼多年,隻去上野公園看過一次櫻花,而且還是和朋友去書店買書,順路經過纔進去的。他在仙臺整整兩年,附近不遠就有一個 的風景區松島,他也隻去玩過一次。回國以後,住在杭州那樣優美的地方,一年間竟隻去西湖遊過一次,還是朋友請的客。別人都連聲稱贊“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卻以為“不過平平”。1924年他寫《論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俶塔弄錯了位置,你當可想像,他平日對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後到北京,住的時間更長,遊玩卻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遊覽名勝古跡,他最感興趣的地方,卻是古董鋪。弄到 ,他甚至公開說:“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 不知道他說這話有多少調侃的意味,倘是講真話,那他是錯了。對自然風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個人的天賦當中,多少都埋有親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隻是由於後來的經歷不同,有些人的這個天性得到激發,變成酷愛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卻遭受壓抑,便自以為對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對優美的自然風景,我們會不會深受感動,這實在可以作為衡量我們的精神是不是正常發展的重要標尺。因此,看到魯迅在廣州和杭州玩得那樣快活,我想誰都會為他高興,他童年時代的善感的靈性,那《社戲》中的天真的情態,終於在他身上復蘇了。
當然,愛情在他身上喚起的,絕不止是親近自然的遊興。一說到愛情,人總會習慣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輕的生命,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容易把愛情看成青年人的專利,許多人鼓吹愛情的 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賦權利嗎?許廣平是那樣一個富於活力的姑娘,又比魯迅年輕那麼多,魯迅一旦與她相愛,這愛情就會對他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要求他振作精神,盡可能地煥發生命活力。倘說在紹興會館時,他自安於“農奴”式的枯守,還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靜來抵擋世俗歡樂的誘惑,甚至克制和壓抑生命的本能衝動;他現在卻 完全改變,要竭力振奮自己的人生熱情,竭力放縱那遭受長期壓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畢竟是男人,魯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總會希望自己是一個富於活力的人,一個能夠讓愛人崇拜的人。他當然有自卑心,所以纔說自己“不配”;?但他更多的是要強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活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輕。事實上,也隻有當這要強心在他頭腦中占上風的時候,他纔會坦然地接受許廣平的愛。隻是這要強心一面允許他擁抱許廣平,一面卻又暗暗地告誡他:你 像個年輕人!?
魯迅本就是情感熱烈之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許多表現自然會洋溢出青年人的氣息。他對黑暗的毫無掩飾的憎惡,他那種不願意“費阨潑賴”(Fair Play)的決絕的態度,都是極能引起青年共鳴的性情。但是,他畢竟又是個思想深刻的人,40年的經歷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種深廣的憂郁,迫使他養成一種沉靜的態度,不喜歡雀躍歡呼,也不主張赤膊上陣。不輕信,更不狂熱,選一處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塹中靜靜地觀察:這正是他到北京以後逐漸確定下來的人生態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層心境的人生態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鬥志,煥發精神,以一種青年人的姿態置身社會,他的言行就往往會逾出其“常態”,顯出一種特別的情味。 比方說,他從來就是個實在的人,說話都是有一句說一句的,可在磚塔胡同的家裡與姑娘們笑談的時候,他卻屢次提到自己床鋪下面藏著一柄短刀,又詳述自己在東京如何與“綠林好漢”們[指光復會中人]交往,言語之間,時時露出一絲誇耀的意味。再比如,到1920年代中期,他對青年學生已經不抱什麼期望,所以“女師大風潮”鬧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觀態度。可是,一旦與許廣平們熟識,他的態度就明顯改變,代她們擬呈文,起草宣言,還一個一個去聯絡教員簽名,組織校務維持會,裡外奔走,口誅筆伐,終至被章士釗視作眼中釘,我不禁想,倘若他並不認識許廣平她們,他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嗎?即便出於義憤,站出來聲援學生,也不過是像聯署那份宣言的馬幼漁們一樣,說幾句公道話了事吧。 同樣,他向來就不大贊成學生請願,不但對“五四”運動作過那樣冷淡的評價,就在1926年3月18日上午,他還硬把許廣平留在家裡,不讓她去執政府門前請願:“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東西等著要抄呢!”?可是,當“3·18”慘案的消息傳來,死難者中間又有他熟稔的女師大學生劉和珍,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連三地寫文章斥罵當局,口氣激烈得近於切齒,我難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對劉和珍們懷有親近的感情,他的反應會不會有所不同?身為這些年輕姑娘的親近的師長,對她們的慘遭屠戮卻全無救助之力,望著許廣平們的悲憤的眼光,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猜想,大概正是這樣的一種心情,纔使他下筆的態度格外激烈,詛咒的口氣也格外決絕吧。推而廣之,他在1920年代中期的公開的文章中,依舊勉力唱一些其實心裡並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經深覺沮喪的情形下,依舊戴著面具,表現出充滿熱情的鬥士的姿態,所有這些“心口不一”的行為背後,是否都有那愛情或準愛情的壓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說,他到廣州與許廣平會合以後,這壓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應該老是神情陰郁,於是他勉力說一些鼓舞人的話,有一次甚至斷言:“中國經歷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朵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有活力的人不但應該對將來抱有信心,更應該投入實際的,許廣平就正是這樣做的,她自己是左派,對“國民”滿懷熱情,於是魯迅藏起他先前那個徹底的懷疑意識,也來熱烈地贊揚北伐,贊揚。尤其是對青年人發表演講,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稱贊廣州是“策源地”,而現在已是“的後方”;他向中山大學的學生呼吁,要他們用“的精神”,“彌漫”自己的生活,“這精神則如日光,永遠放射,無遠弗到。”。?他更說自己“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在一次演講會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門,大聲號召說:“廣東實在太平靜了,我們應該找刺激去!不要以為目的已達,任務已完成功時說的,可以過著很舒服的日子!?讀著他這些激進的言辭,我仿佛能想像到當時的情景:一個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著臺下年輕聽眾們的熱切的目光,用紹興腔提高了嗓門大聲呼喊——為了煥發青春的氣息,他的確是盡了全力了。這也自然,身邊有許廣平,四周又是初到廣州時的青年人的熱烈的歡迎,任何人處在這樣的境遇裡,恐怕都不免要興奮得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吧。 (此處空一行)
但魯迅畢竟不是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了。1927年舊歷初三,他和許廣平等人漫步越秀山,當踏上一個小土堆時,也許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身手還健,他執意要從那土堆上跳下來。他是跳下來了,但卻扭傷了腳,半天的遊興,就此打斷。這腳傷還遲遲不肯痊愈,半個月後他去香港作演講,還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費力。不知為什麼,每當讀到他在廣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辭,我總要想起這件事,它似乎是一個像征,既表現了他的心情的活潑,更表現了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他45歲纔嘗到愛情,以當時人的一般狀況,已經太晚了,他無法像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那樣忘情地擁抱它。在整個1920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惡意去揣測世事,要他單單在爭取個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備的盾牌,他實際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決意和許廣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顯示一種勇敢的姿態,他內心還是相當緊張。
這緊張也井非無因。就在他到廈門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間已經有一種傳聞,說他和許廣平同車離京,又從上海同船去廈門,“大有雙宿雙飛之態”。?他們還沒有同居,議論就已經來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飛舞到怎樣。事實上,1928年2月,他和許廣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過這樣一封信:“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關繫,……此事關繫先生令名及私德,……於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寫信人自稱是崇拜魯迅的青年,卻如此看待他和許廣平的愛情,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會上永遠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眾,你就是再循規蹈矩,謹小慎微,隻要你是名人,就總會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惡意跟蹤而來。干脆想通了這一點,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魯迅同輩的文人中,就頗有一些人是放浪灑脫,無所顧忌的。但是,魯迅做不到這一點,愈是心中“鬼氣”蒸騰,愈是把社會看得險惡,一點小小的流言,就愈會引發他廣泛的聯想:形形色色的遺老遺少的攻訐,報章雜志上的惡意或無聊的渲染,學界和文壇上的有權勢者的封鎖, 是經濟上的拮據和窘困:他已經很難擺脫那個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劇的夢魘了。?
正因為心頭總是壓著那個夢魘,魯迅和許廣平同居之後,依然左盼右顧,如履薄冰。他將許廣平的臥室設在3樓,自己則住2樓,對外隻說她給自己當助手,作校對,除了對極少數親近朋友,一概不說實情。即便去杭州,實際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動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預訂1間有3張床的房間;到了杭州,許欽文等人接他們到旅館,住進那房間後,正要離開,他卻喚住了許欽文,眼睛盯著他,“嚴肅地說:‘欽文,你留在這裡。以後白天有事,你盡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他並且 許欽文睡在中間那張床上,將自己和許廣平隔開——這是怎樣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勵許廣平到中山大學給他當助教,口氣是何等堅決:“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對語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可你看他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嗎?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樣快活,看到他晚上這樣睡覺,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輩子都沒有真正放松過吧,陪伴心愛的女人到西湖邊上度蜜月,都會如此緊張,這是怎樣可憐的心境,又是怎樣可悲的性格??
這樣的緊張一直持續了很久。從一開始,許廣平就沒有向親屬說過實情。直到1929年5月,她已經懷了5個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纔將實情告訴她,並請她轉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魯迅這一面,也是從這時候起,纔陸續告訴遠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報,口氣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給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寫信,說那些流言如何氣人,於是他索性“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房子裡——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這哪裡隻是通報,中間夾著這麼多解說,而且到了 還是含含混混,並不把事情說清楚。也許他並非存心如此?那麼,心裡明明想告訴別人,寫出來卻這樣吞吞吐吐,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許廣平將實情告訴姑母後,對魯迅說:“我的親人方面,如由她說出,則省我一番布告手續,而說出後,我過數月之行動[指生產]可以不似驚弓之鳥,也是一法。”?什麼叫“驚弓之鳥”?莫非在下意識裡,他們自己也並不真能坦然? 一個人受多了壓抑,就容易喪失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連評價自己,也會不自覺地仿照周圍人的思路。尤其當與社會習俗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應該理直氣壯,心理上還是常常會承受不住,不知不覺就畏縮起來。魯迅和許廣平這“驚弓之烏”的緊張,是不是也正來源於這一點呢?當然,他們願意將消息公諸親友,總還是因為有了信心,你看魯迅這時候寫給許廣平的信:“看現在的情形,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對許廣平的呢稱]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就明顯表露出終於松了一口氣的輕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後,纔剛剛松這一口氣,他們先前的屏息擔心,未免也太過分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和許廣平相愛而終於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舉動之一。正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生命意志的執拗的力量,表現了背叛傳統禮教的堅決的勇氣,表現了一個現代人追求個人自由的個性風采。但是,也恰恰在這件事情上,他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他對傳統道德的下意識的認同,他對社會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現得格外觸目。人一旦相信愛情,就不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魯迅能夠打開一個缺口,也就應該可以衝出“鬼氣”的包圍:如果這樣來看,他和許廣平的同居就正顯示了他對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但是,他在衝出包圍的途中,要經歷那麼多的猶豫和權衡,這會不會使他終於爭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覺就變了味呢?男女愛情,這本是為人的一項基本樂趣,倘若你 要耗費那麼長的生命,經歷那麼深的痛苦,纔能夠獲得它,你還能說它是一項樂趣嗎?用太多痛苦換來的幸福,它本身已經不完全是幸福,它甚至很容易變成一筆債,將承受者的脊梁壓彎。因此,一想起魯迅硬拉許欽文同眠一室的情景,我先前那因他們同居而產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魯迅是獲得了勝利,可恰恰是這個勝利,宣告了他可能難得再有真正的勝利。  ? 一部影響深遠的魯迅思想傳記,代表了20世紀十年代知識界努力衝破啟蒙話語,力圖回到“魯迅本身”,從個體生存的心理結構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讀魯迅的重要嘗試。 作者以魯迅的人生歷程和思想發展為經緯,以其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鬼氣”和“絕望”為主軸,把魯迅思想氣質中的懷疑、矛盾、陰郁乃至黑暗刻畫得深入骨髓,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會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鳴中,感受到作為一個人的魯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劇。 作者曾解釋如此理解魯迅的原因,是“想要打破那一味將魯迅往雲端裡抬的風氣,想要表達對魯迅的多樣的情感,不僅僅是敬仰,是熱愛,還有理解,有共鳴,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讀者顯示生活的復雜和艱難,不僅僅是魯迅,也是我們自己,不僅僅是過去,也是現在和將來”。  
王曉明,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繫、中文繫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 ^_^:000673668c18dc27521f79a0f5def5f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