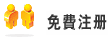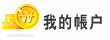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 | | | 蔓草綴珠(增訂版)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 【市場價】 | 608-880元 | | 【優惠價】 | 380-550元 | | 【作者】 | 陳早春 | | 【出版社】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 【ISBN】 | 9787020127986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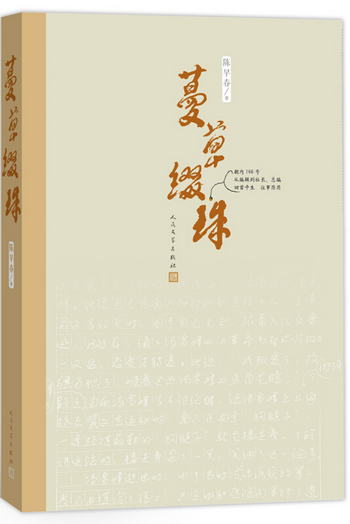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9787020127986 版次:1 商品編碼:12243843 品牌:人民文學出版社(PEOPLE’S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出版時間:2017-1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20 字數:332000 作者:陳早春
" 內容簡介 當今寫散文的人很多,據說流派也很多。中國人很注重招牌,就是賣點家常酒,也要高高地挑出個酒幡子。“我”寫的這些篇什,也許不入流,因此也就無所謂派,隻是對寫的對像心有所思,潮有所湧,就寫了,有無技巧,未曾追求過,因此也就不知道。
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大都是有關自己的心路歷程以及親情、友情的記述和回憶,是所謂回憶散文。人到回頭看以往征程的時候,大抵是已進入生機不旺的暮秋季節了。“男兒本自重橫行”,臨到一步一回首去“臨晚鏡,傷流景”的時候,已是沒什麼出息的了。好在回憶過往時,撫摸一下已愈或將愈的傷疤,也是一種慰藉甚至樂趣。回憶是為了忘卻,忘卻是一種解脫或超脫。人之所以愛看悲劇,蓋由於此也。至於回憶中自然要涉及到過往的人事,環境甚至時代的側影,世事的痕跡。
增訂本沿襲《蔓草綴珠》的編法,隻將新寫的編入同類中。個別篇增寫了題注和補記。同一件事在不同文章中重復的事,則予以刪除重復部分。而王笠耘、張嘉興的信函,不另行置於附錄欄內,而附在有關文章後面。
目錄 自序
增訂本序
童子軍裝——憶母親
我的朋友
心祭
父親二三事
無情的父愛
六親不認的小胖胖
送方方歸國瑣記
家鄉的小橋
竹筍贊
“偷”的憶念
野孩子的野趣
我的文學緣
迫不得已的出風頭——“五七”干校生活點滴
知識的饑餓——憶大學的開頭兩課
啞然失笑的痴情
書房的尷尬
新隆中學·隆回二中憶往
牛汀掠影
追憶馮雪峰的晚年
漫憶包子衍
馮雪峰與我放鴨子
不像“長”和“家”的樓適夷
我的初小老師
我看君宜同志
回望雪峰
冷清地活著,又冷清地走了——憶林辰同志
非師非友、亦師亦友的蔣路同志
不應遺忘的角落——記張嘉興老師
附:來信來文各一
懷念顏雄
為魯迅代筆——近四十年前聽馮雪峰閑聊
編輯家牛漢瑣記
在人文社領導層中的李曙光
出版界的老黃牛王仰晨
折翅仍在飛翔的舒蕪
編輯龍世輝
張琳,應該請入人文社“凌煙閣”
孫用晚年行藏拾記
多面手王笠耘
附:王笠耘來信一束
樓適夷——一個純真的人
聊答李霽野先生
附:幾則通信
說“小”議“大”
“名著熱”的襲擊
大師的教誨
造名術記略
會海無涯,何處是岸
論喫飯之難
人走茶自涼
鄉思
訪臺三願
感受尼亞加拉瀑布
杜荃是誰
附:徐慶全《“杜荃(郭沫若)”——驚動高層的<魯迅全集>一條注釋》(摘錄)
《英烈傳》校點說明
致朱正——奉《魯迅傳略》稿審讀意見
《綆短集》編後記
《續英烈傳》校點說明
《中國文史人物故事書箱》出版緣起
《馮雪峰評傳》修訂後記
《激戰無名川》出版記
《法律行者》序
《李吉慶裝幀藝術》序
賀《網聚鄉情》出版(代序)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馮雪峰與我放鴨子
一九六九年九月,為了“備戰”和“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人民文學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數幾個人搞“樣板戲”之外,終止了業務,無論“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也不管老弱病殘,都被“全鍋端”,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去圍湖造田。其時,馮雪峰已六十七歲了,他佝僂著腰,戴著“黑幫”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
開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組種菜,這比起圍湖造田、打壘建房等重活來說,算是輕松的了。其實不盡然:翻地開畦,運肥潑糞,彎腰蹲地侍弄幼苗,對那些老弱病殘者來說,也是不堪重負的。一天下來,就著床,既難躺下,也難爬起。特別是陰雨天,黏稠得像糯米粑的黃泥巴,好像有意與他們作對,使他們有如蜘蛛網上的飛蛾,動彈不得。馮雪峰由於出身農民家庭,又參加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喫過小米,扛過步槍,蹲過監獄,在各種磨難中淬過火,因此在這個組裡,干得十分出色,連最好挑剔、以找碴兒為職責的某軍代表,也在人後嘖嘖地稱贊過這個瘦弱的老頭:“他比我長期在農村勞動的祖父還精干!”
當時,我正在當“鴨司令”,放養二百多隻母鴨。這些鴨子,是當地大棚裡篩選下來的處理品,一隻隻毛孱孱的,吝嗇得一個蛋也不肯下。經我幾個月的調養,且不費飼料,春末的下蛋率竟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保證“連”內每個“戰士”每天可以喫到一個鴨蛋。這對連續啃了半年多咸菜疙瘩、不沾油葷的“喫齋”隊伍來說,無疑是件大恩大德的善事,引起了軍代表和連干部的十分重視。他們向我說:“你每日早出晚歸,櫛風沐雨,夠辛苦的,需要一個助手;再說,你懂得整套農活,大田還需你去指揮,放鴨的事,你培訓培訓,今後就交給你的助手。”我當然同意,但當知道這個今日的助手、明日的接班人就是馮雪峰時,我卻猶豫了:第一,馮雪峰做過胃大切除手術,下到干校後,經軍代表特準可以買餅干來維持生命,若在湖裡放鴨子,一日三餐不準時,且都是涼的,他能否承受得了?第二,湖裡夏天烈日當空,沒有任何遮攔,氣溫高達四十幾度,寒鼕北風刺骨不算,時不時會掉進水裡成為落湯雞,年近七旬的老頭,受得了這份罪?第三,湖地的田埂都是爛泥搭的,水蝕霜凍後,就成了豆腐渣、爛漿糊;烈日一曬,又成了見稜見角、有鋒有刃的死硬疙瘩,矯健的年輕人都難免摔跤,將他的老骨頭摔斷了怎麼辦?我的擔心向上級說了,但沒受理,因為我屬“連隊戰士”,服從命令是天職。
一九七○年初秋,鴨子經過“夏眠”後又到了下蛋的季節,這時馮雪峰從蔬菜組調出,來到我的麾下報到。本來,他已是我的老“部下”了,當“文化大革命”進入到“大聯合”階段時,“牛鬼蛇神”除中央另立專案者外,一律下到革命群眾中接受“監督改造”。其時,我是現代文學聯合小組組長,馮雪峰下到我這個組接受“改造”。我的“革命性”不強,歷來屬於“中右”,而他又讓你怎麼翻來覆去地看,都不像個階級敵人,所以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監督改造”與反“監督改造”之間的鬥爭。當時好抓“苗頭”與“新動向”,在我們組裡,連這些也沒抓到一絲一縷,很令革命者失望。
他奉命來到我身邊,一見我隻穿一條短褲衩,通體像醉蝦一樣紅中透黑,便善意地忠告我:“早春,這地方的太陽很毒,你得戴個草帽。背心總得穿一個纔是。”我說:“光棍一條,為的是圖方便,也為了偷懶。天晴讓它曬,雨天讓它淋,不用換衣服;有時我還得跟鴨子在水中賽跑,下水無需脫衣服。”他聽我這麼說,沉默了一會兒纔沉吟道:“我老了,不行了,今後不僅幫不上忙,還可能給你添累贅。”
我們的衣著打扮是個明顯的對照。他戴著草帽,腳蹬膠底跑鞋,身著那套似乎從來沒有更換過的灰不灰、白不白的舊卡其布制服,隻是袖管和褲管都卷了起來,胳膊和腿都顯得特別瘦,特別長,像干枯的松樹枝斜插在他的軀干上。這樣的老頭,今後要跟我在這四無人煙也無林木飛禽的湖地裡經歷酷暑嚴寒,真令人心酸眼澀。
一看他這身軀和打扮,我不敢也不忍讓他作我的助手和接班人,但我極願意有個伴。我自放鴨以來,從每日睜眼到閉眼,都是在湖地裡望著蒼茫茫的天,汪洋洋的水,追隨著鴨子度過的。見不到人,也見不到飛禽走獸。每當鴨子喫飽了,在戲水涮羽毛、將扁嘴埋進翅膀窩裡睡覺時,我便寂寞得無聊。有時萬念俱灰,人好像是在羽化,在寂滅;有時為了驅趕寂寞,便去捕捉青蛙或蚱蜢,聽它們的叫聲,看它們的掙扎。
馮雪峰並不甘於作為我的伙伴,他一來就要領任務:“我小時在農村,什麼農活都干過,就是沒放過鴨子。這鴨子該怎麼管纔能管好,讓它們下蛋?我該幫你干些什麼事?”我如數家珍地向他傳授了養鴨子的經驗,至於他的任務,我不太經意地說:“一切有我照管,你隻幫我看著它們點,不要讓它們瞎跑,或掉了隊,或往禾穗已勾頭的稻田裡竄,毀了莊稼。”
他領了任務之後,就馬上去鴨群邊尋找自己的崗位。當時鴨子已喫飽,在水窪邊睡覺。我叫他不要去驚動它們。他還是躡手躡腳地往鴨群邊靠,死死地盯住它們,生怕它們一展翅就飛跑了似的。
鴨子醒過來了,在水窪裡戲水。馮雪峰很緊張,圍著水窪來回跑,任我怎樣制止也無效。看來他將我交給他的任務牢記在心,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太陽偏西了,為了讓鴨子晚上飽餐以過夜,我將它們趕入深水中去限食(行話叫“限”)。“限”到一定時候,鴨群開始騷動、嘩變,餓慌了的四處亂竄。馮雪峰見此情景,緊張、慌亂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揮舞著鴨竿,顧此失彼地應接不暇。
鴨子在深水中“限”了兩三個小時,太陽已靠近地平線,該是讓它們進食的時候了。我吹了幾聲口哨,鴨子拍打著水,“嘎嘎嘎”地叫著向我飛撲過來。我將它們引至一塊剛收獲過的稻田,這裡有稻粒、草籽、蟲蝦和田螺等,可讓它們葷素搭配著飽喫一頓。
馮雪峰見到了剛纔的一切,感到了千斤石頭落地樣的輕松。他說:“看來我的緊張是多餘的,鴨子都聽你這個司令的指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何苦要我多操心!”
話剛落音,鴨子已進入田中覓食了,一下子他又急了,簡直是急瘋了。他佝僂著腰,沿田埂瘋跑,摔倒了,又爬起急跑,又摔倒了……這樣反反復復多次,土疙瘩、鴨竿都與他作對,將他絆倒。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開始以為是鴨群中出現了黃鼠狼,讓我也緊張了一陣子。過了好久,我纔弄明白。原來,經限食的鴨群,一到覓食的地方,為了調查了解食物的情況,也為了爭奪覓食的有利地盤,下田伊始,就低著頭,聳著尾,做好衝刺的準備,至少跑遍一匝纔肯落嘴。馮雪峰不了解它們覓食的規律,一見到這情景,擔心它們跑飛了,所以纔拼命地追趕、堵截。他時時刻刻都在記著他的崗位和職責。
他放鴨第一天的戰績不佳,付出的代價卻很高:腳手都掛了彩,衣褲甚至頭發都漿上了泥沙。
他付出的代價也得到了一點補償。第二天清棚撿蛋時,白花花一片,二百零六隻鴨子下了二百零三個蛋,鴨子報答了這位老人。這老人看到這一豐收景況,像小孩一樣,天真地開懷大笑。
以後兩天日子過得還算太平,鴨子乖乖地聽指揮,我們也贏得了清閑,可以聊聊天。我想利用這樣的機會,在沒有第三者在旁的情況下,無所顧忌地向他請教一些問題,如他與毛澤東、魯迅、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的交往,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多次爭論,以及他個人爬雪山、過草地、蹲監獄等傳奇般的經歷。我提的問題很多,但他幾乎不接應這樣的話題,要麼說,這些已寫過材料了,要麼叫我去看某某革命組織印發的文章或資料。我感到,雖然他已兩度作為我的“部下”,但他屬“黑”,我沾“紅”,分屬兩個營壘,雖然在干校,“紅”與“黑”已不像“文革”高潮中那樣涇渭分明了,大家同屬“天涯淪落人”,但“防人之心不可無”啊。他不願說,也許還因他不願在過往的日子中討生活,翻瘡疤,他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向他提的問題沒有得到反應,倒是他向我提了許多有關放養鴨子的問題,我都一一作了說明。我滔滔不絕地說,他專心致志地聽。他越是聽得認真,我就越說得有興,以這樣的“高堂講經”打發無聊的時光。有一次,他插話問我:“你很小就離開農家,也沒有放養母鴨的經驗,為何取得了這樣高於鴨師傅的成績?”我不假思索地說:“黨把我培養成知識分子,本想干點文化工作,從來也沒想到還會返回去當農民,當鴨師傅。我干得再好,對黨對己都是個損失。但命運既然做了這樣的安排,個人改變不了。怎麼辦?要麼苟且偷安,要麼玩世不恭,要麼憤世嫉俗。我不願這樣混和闖,隻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愛一行,鑽一行。從干中實現自我價值,尋找人生樂趣。目前我不能與人交往,就與鴨子結伴,觀察它們,了解它們,研究它們的生活規律,從這種研究中寄托愛心,鍛煉已經生鏽了的思維。不然,我整日在這荒無人煙的湖地裡,被動地經酷暑、歷嚴寒,不被環境戕害死,也會自己悶死、憋死……”他聽了我這席話,頗有感觸地說:“這是一種人生哲學!抱這種人生哲學的知識分子不多。的確,有人認為這樣的人是安貧樂道的庸俗之輩,或是不反抗命運的奴纔。但什麼叫俗人,什麼叫奴纔,都是那些懷纔不遇、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詮解的。這些人到底有無纔,還是個問題,往往自認纔富五車的人,說不定他的纔還不夠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這樣的人,大事干不來,小事不願干。寶刀可以斷鐵,豈不能斷木!鉛刀還應一割哩。我曾經說過,人世間有在高堂應對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燒火做飯的奴婢;有日馳千裡的車子,必得有鋪路的灰砂碎石。魯迅曾經寫文章界別過‘聰明人’、奴纔和傻子。我看,世界上多的是‘聰明人’,奴纔也不少,缺乏的是傻子。如果多些傻子,世道就好了。”
自這次不經心的交談之後,我們之間那堵“紅”與“黑”的牆,慢慢地變小了,變矮了,特別是自干校回到機關之後,我們成了忘年交。這種變化,也許跟這次交談不無關繫。
很可惜,我們在干校相處的日子不很長。大約是在他來放鴨的第四天,就發生了一起影響他放鴨生涯的事。他從此再不作我的助手,更沒能做成我的接班人。
這天下午,我們在鴨子限食的時候,天南海北地聊天,待我吹哨將鴨群召上岸時,發現少了近三分之一的鴨子。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便將上岸的鴨子交給馮雪峰,讓他獨自照料它們覓食。我卻縱身跳下水去,遊向肉眼不及的湖汊處,去尋覓脫群的掉隊者。然而尋遍所有的湖汊都沒找到,後來在一片稻田中傳來了窸窸窣窣的響聲,上岸就近一看,它們正在絮絮地偷食稻穗。由於時近垂暮,它們戀食不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將它們趕了出來,逐向湖中。待我將它們趕歸鴨群時,天已蒙蒙黑了。馮雪峰還在等著我,費勁地在攔阻、堵截早想上路歸棚的鴨群。我見此情景,禁不住說了幾句硬話:“到這個時候了,你應該隨機應變,先把這批鴨子趕回去,何必死死等我!”他沒有分辯。不難看出,他在自責自咎。我為了緩和緊張空氣,便說:“沒事。鴨子不像雞,不患夜盲癥,隻要有點月光,它們會回棚去的。”
考慮到鴨子熟悉我的身影,由我在前面引路;為防掉隊者,由馮雪峰殿後護駕。長長的一列隊伍開撥了,在浩浩蕩蕩地前進著。待我將它們放至鴨棚時,卻不見了馮雪峰。我趕忙返回去找人。拐了一個彎,下了一個坡,在一條水溝邊聽到了鴨叫聲,卻不見人影。待我聞聲找去,隻見馮雪峰在水溝中一手捏著三隻鴨子的脖子,另一隻手在草叢中既摸且按。驚恐的鴨子隻躥不叫。我下到水溝中摸住了這隻鴨子,並扶他上了溝岸。催他往回走,他卻蹲在岸上不動。我擔心他摔傷了走不動,他說沒摔傷,隻是擔心還有掉隊的鴨子沒發現。我告訴他,掉隊的鴨子會叫喚,除非踫到了野獸。他這纔放心地跟著我回去了。待到燈光下一看,他全身都是泥濘,膠鞋也掉了一隻,原有的傷口又在滲血了。
次日清晨,他按時趕到鴨棚,也照常跟我趕著鴨子下到湖地,但他整整一天再無興致向我請教鴨經了,幾次向我提出:“我腿腳不靈便了,趕不上鴨子,你給我的任務勝任不了。昨晚上我犯了錯誤,今後還難免再犯。為了不給你添累贅,也為了鴨群得到更好的照料,我想請求調回原組去種菜,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請你代我向軍代表、連干部請求一下,就說我干不了,干不好。”
這事引起了我很久的思索,如果馮雪峰是個苟且偷安的人,巴不得在我這棵樹下乘涼,天塌下來有“司令”頂著,管它那些閑事;如果他是一個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人,正可拿鴨子來撒氣,鴨子丟了、死了,其奈我何?但他卻傻子似的忠於職守。他來放鴨子,是出於一種責任心,他請求免除這差事,也是出於一種責任心。
由於我有這種考慮,也由於人所應有的對一位老者的同情心,馬上向軍代表和連干部轉達了他的請求。好在他們並不懷疑馮雪峰的勞動態度,沒有“抓階級鬥爭新動向”,同意了他的請求。沒過幾天,就將他調回原組去了。我有點惋惜,但也慶幸他從我這裡得到了解脫。不然,像他干事這麼認真的人,哪怕隻與我一起再經歷一個秋去鼕來,也許不要等到一九七六年,在干校就得向他的遺體告別了。
……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蔓草綴珠自序
十多年前,一位也算是相當托熟的同事,曾直言不諱地說我“隻開花不結果”,至今也未知何所指。其實,我從未露過“尖尖角”,沒開過花,更不用說結果了。
聽說一位在國內享有很高聲譽的作家,曾向我的同事為我抱屈過,說讓我干那些雜事是“浪費人纔”。意謂我是個“人纔”,則更不敢當了。其實,我隻能是個苦力,叫干哪行就干哪行。
寫作這一行,從來就不是我的專業,不是領導分給我的任務,至今仍然如此。記得一九八一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時,在北京要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為北京“三魯”之一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因沒有論文提供,不能與會,同事們的心態有點不平衡,公推我去趕寫文章爭出一口氣。既是趕寫,就得占用一點工作時間,呈請社領導準假。領導批得相當干脆:“不準!”我隻能開六個通宵的夜車,完成了一篇三萬六千多字的論文。文章在《中國社會科學》刊物上發表了,也被這次學術討論會采用了,因而爭來了幾個與會的名額,算是為大家爭了口氣。可是我卻差點使自己斷了氣。寫下文章最末的一個字,就暈倒在沙發上,半天起不來,可見干編輯這一行,得安分守己,硬拼不來的。
俗話說:“木匠家裡凳沒腳,和尚家裡鬼唱歌。”為人家做嫁衣裳的我輩大都難得為自己做幾件好衣裳,當然天纔例外,不是坐班的非專職者例外。但自己終究是個文字工作者,稍有空閑,就難免心掛撓鉤,手也癢癢,時不時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整天這點屬於自己的時間,去塗鴉稿紙。開始是結合工作,在別人的文章裡看風景,撿遺漏,寫一些所謂學術性的論文,說得冠冕堂皇一點,是結合工作搞研究。領導也不好說什麼,因為用不著他們勞神去審批請假條,肚子裡的腹稿,B超也看不著。那時寫作欲望極旺,計劃寫個三五本書,還為一大學牽頭領了個國家社科研究項目。可是正當此時,卻被民選為單位頭頭,而且是個主管全面工作的頭頭。雖然三次打上門去,向主管機關請辭而未果,被趕著鴨子上了架。上了架就下不來,被煙熏火燎烤了十多年。好容易因年邁出爐了,結果可想而知。自上架之後,幾乎終止了寫作,一部已在刊物上連載了兩年的書稿,不得不被自己腰斬了。
我是一介書生,自己尚且料理不好,怎能去管別人。所以這個頭頭當得很苦,哪還有寫作的靈感,伏案的時間。加之自己是個死心眼,叫背犁就背犁,叫當驂馬絕不當轅馬。守著本分,心不旁騖,不會彈鋼琴,不會抽空去種自己宅前宅後的那三分地。
我沒有當過散文編輯,沒有受過名家的熏陶,沒能濡染散文的大千世界,原本就沒想要寫散文,更不敢以散文名世。後來也居然寫了一些,這得感謝我所在單位的一些老編輯。他們除干自己的本行外,大都兼擅寫作。一次,為宣傳計,我為香港一作家的創作,寫了一篇豆腐干式的文章,在香港某報發表了。自己寫了也就忘了,沒有留剪報。但有同事見到過,於是勸我:“你太忙,大塊論文沒時間寫,就抽空寫點散文吧。你的評論文章寫得像散文,耐看。”曾是我上級的一位著名詩人幾乎一見面就勸我:“雜事少管些,多寫點文章吧。”有一位早已退休的同事隻要見到我發表的散文,就要犯職業病,給我來信,“奉告”他的審讀意見。在他們的催促鼓勵下,我也就斷斷續續寫了些急就章。可是越寫越不敢寫了。散文似乎誰都可以寫,但要寫好的確很難。它是普普通通的蘿卜、白菜,不是名廚,很難做出口味來。
當今寫散文的人很多,據說流派也很多。中國人很注重招牌,就是賣點家常酒,也要高高地挑出個酒幡子。我寫的這些篇什,也許不入流,因此也就無所謂派,隻是對寫的對像心有所思,潮有所湧,就寫了,有無技巧,未曾追求過,因此也就不知道。
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大都是有關自己的心路歷程以及親情、友情的記述和回憶,是所謂回憶散文。人到回頭看以往征程的時候,大抵是已進入生機不旺的暮秋季節了。“男兒本自重橫行”,臨到一步一回首去“臨晚鏡,傷流景”的時候,已是沒什麼出息的了。好在回憶過往時,撫摸一下已愈或將愈的傷疤,也是一種慰藉甚至樂趣。回憶是為了忘卻,忘卻是一種解脫或超脫。人之所以愛看悲劇,蓋由於此也。至於回憶中自然要涉及過往的人事環境甚至時代的側影,世事的痕跡。雖然時過境遷,大都是模糊不清而泛黃的舊影像,但不敢冒充時下看重的老照片。
除這類散文之外,還收輯了一些隨筆、雜文和書籍的前言後記等。古代武士講究十八般武藝,木匠也得學會劈鋸刨鑿各行,並行行都會。唯其不會纔試著去學哩。
也許是由於這些原因,這些急就章,居然還有些許讀者,特別是中學語文教師這個階層的讀者。記得我的散文剛發表十數篇時,一位曾是高中語文教師的北京廣播電臺的主持人,就曾兩次將它們配樂廣播過。最近我因外出,兒子還代我與一家音像公司簽了一份將錄制拙作的協議。聽說某些篇章已選入中學教科書。
這些文章大都構思或成篇在月黑星稀的夜晚。這時,萬籟俱寂,大千世界似乎沒有了生機,隻有野蔓卻在充分利用地氣,釀造滿莖滿葉的露珠。我自忖不是園圃中有科目可屬的花卉,更不是高山峻嶺中的參天大樹,隻是野地裡的一縷蔓草。蔓草長在路邊、田邊,地不分肥瘠,都有它的蹤跡。它不與同類爭奪空間,無需人工侍候。它無花可供欣賞,也沒有果實可飽口腹,隻無償地為大地點綴一點綠色,並為晨曦奉獻自己身上的點點滴滴。對此,古人就曾吟詠過:“野有蔓草,零露兮。”我心儀這野蔓上的露珠,就將書名叫作“蔓草綴珠”,算是敝帚自珍吧。
這些文章,大都在報刊上發表過或即將發表,基本上保持原貌,有個別篇改了題目。輯集時,大致以類相從,類中則以文章發表時間先後為序。後面附有兩組來信,它們都是品評或專門點評拙作的,似可代做名家的序言或專評。在我看來,它們寫得隨意而實在,對一般讀者來說,也許較為實用。當然,其中難免有過譽之詞,讀者千萬別上當。
增訂本序增訂本序
《蔓草綴珠》於二○○五年出版後,不斷有親朋好友向我索要,特別是南方的故舊,說是跑遍書店都尋覓不到,於是我就請身邊的好友去網上搜索,也沒能如願。一次,與同事郭娟女士說及此事,本是希望她在網上留意為我搜索一下,她卻說,它既是人文社出版的,何不再版一次,有電子版,再版很容易。我說原電子版是在社外排的,搞得很亂,當時連校樣都很難看下去,原版不能再用,得重排。重排得勞民傷財,加之現在讀者都在玩手機,成了“低頭族”,很少有人正襟危坐去埋首故紙堆。而出版社又成了企業,上面年年下達創利指標,所在職工又得養家糊口,而我們這代人,又無能寫出嘩眾取寵的華章,如果這樣再版,肯定是賠錢貨,坑出版社一把,於心不忍。未曾想到,社領導積極推動,社長並已簽備了出版合同。於是出書的事,又在心頭活泛了起來。曾經擬出版一本新作,叫《人文社群星掠影》,連前言都寫好了。如果出版這樣一本新作,趁便搭上《朝內166號》的順風車,也許還有點銷路。因我生正逢時,在朝內166號待了四十多年,認識那裡的幾代人,原《蔓草綴珠》已寫了一批老領導、老同事,前幾年又斷斷續續寫了十來人,合起來,分量已足夠了。但這樣做,又怕怠慢了原《蔓草綴珠》的一批讀者。該書出版時,雖未登廣告,未作任何宣傳,所印的五千冊,不到一個月,就被搶光了,可能隻在北京一地,外地的讀者沒有見到。為了顧及這部分讀者,經編輯部同意,就出版它的增訂本。
增訂本沿襲《蔓草綴珠》的編法,隻將新寫的編入同類中。個別篇增寫了題注和補記。同一件事在不同文章中重復的事,則予以刪除重復部分。而王笠耘、張嘉興的信函,不另行置於附錄欄內,而附在有關文章後面。
此書得以出版,首先得感謝社領導管士光、劉國輝和一再加鞭力促並任責編的郭娟。我的糟糠之妻為我復印資料,東奔西突,為之收拾打包。而且她作為文章的第一位讀者,直說她的讀後意見。好在她是自家人,就用不著客套致謝了。
2017.2.22日
查看全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