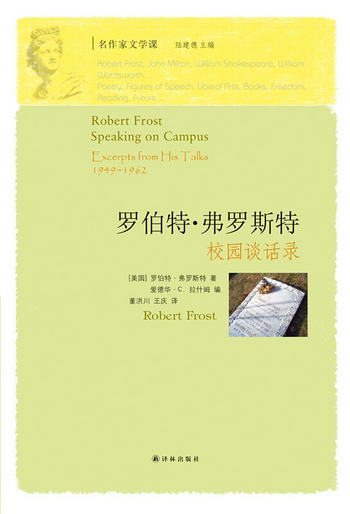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50257 版次:1 商品編碼:11782486 品牌:譯林(YILIN) 包裝:精裝 叢書名:名作家文學課 外文名稱:Robert 開本:32開 出版時間:2015-07-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33 正文語種:中文 作者:羅伯特·弗羅斯特,愛德華·C.拉什姆,董洪川,王慶
" 編輯推薦 《羅伯特·弗羅斯特校園談話錄》首次精選弗羅斯特一生四十多次校園談話的精彩內容。這些談話“純屬漫談”,“沒有講稿”,是“非書面文章”,卻包含了許多真知灼見,展示了詩人在詩歌中無法表達的精神世界。弗羅斯特以談話的方式生動流暢地演示了他所謂“語詞的細微之處”,再次證明了“所有的情趣來自於你如何言說一件事情”。
內容簡介 《羅伯特·弗羅斯特校園談話錄》收錄了羅伯特。弗羅斯特在三十多所院校授課或談話的文稿,時間跨度達三十年之久,是了解和研究弗羅斯特的難得資料。這些談話內容由《羅伯特·弗羅斯特詩集》的編者E.C.拉什姆選編,並由獲普利策獎新聞記者D.M.謝裡布曼作序。書中充滿了智慧與洞見,猶如山澗的清泉,汨汨湧動。
作者簡介 羅伯特·弗羅斯特,是一位罕見的文學大師,在他的世紀裡,隻有威廉?福克納能他比肩。他是二十世紀最受歡迎的美國詩人,曾獲得4次普利策獎,被稱為美國文學中的桂冠詩人。
精彩書評 ★他給美國人民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詩歌寶藏,美國人民將永遠從他的詩行裡獲得快樂和知性
——美國總統約翰·J.肯尼迪
目錄 序言
堅持己見
詩自何處來
巧用修辭
“文科之隱憂”
一切皆有書指引
不是擺脫束縛,而是擁有自由
談談快速閱讀及我們所稱的“完整”
不能讓自己驚奇的,怎能讓別人驚奇
帶著“編織物”前行
世間萬物,正反相隨
弗式詼諧
談談“最大的憂慮”
信念如何鑄成
生活必有所依,直至被代替
某種賭博——無法確定的事情
世界的未來
慢慢求索,直到有所感悟
當寫詩的時候,我想自己在做什麼
論“選舉者”與“當選者”
一見鐘情
談談歸納
“站在新的起點”
某種莫名的焦慮
關於思考和在閃耀中毀滅
優雅地關注美好的事物
讓我們勇敢地說出——詩歌價值無限
聽我說——我的人生足跡
編者後記
引用文獻出處
譯後記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不能讓自己驚奇的,怎能叫別人驚奇
1956年4月4日,弗羅斯特先生在俄勒岡州大學發表演講。本文節選自該演講。《尤金紀事衛報》報道了演講前的新聞發布會,報道這樣開頭的:“詩人弗羅斯特,這位普利策獎的四次獲得者,周二坦言在所得稅申報表上,他從未將自己的職業表述為詩人。”該報援引了他的解釋:“我曾經極力繞開‘詩人’一詞,隻填寫‘農夫’或‘教師’或‘退休者’。我把‘詩人’這一稱謂看作是一個不能用來自我形容的贊譽之詞。”
當我在教書的時候,像其他一些人一樣,抱有如此希望:一年大約隻開設十個講座。我想享受大學裡的特權:一年隻舉辦十次,十二次,最多十五次的講座;諸如此類。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彙報,我寧願永遠不走進課堂。這些事或關於我的親身經歷,或關於我腦海的想法——不論哪種,都有特別之處;它們可以是思想的冒險,也可以是社會或同伴之間的奇遇。
我記得曾想對學生這樣說:“自我們上次見面後,你們又有什麼經歷嗎? 又發生了什麼新的事情嗎?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們我踫到的事情——哦,可能該說成是我想到的事情,而不是我踫到的事情;我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具有價值。
我曾經嘗試如此教學。我說過,“進步”教育的最佳詮釋是——如果連我都不感到驚奇的事情,我將決不告訴任何人、任何學生。不讓我驚奇的,怎讓別人驚奇。人們說,“作家不流淚,讀者就不會有淚。”作家沒有激情和快樂,讀者亦不會獲得愉悅。
如今有個怪事,在各色各樣立志成為和我一樣重要的人士當中,有人把寫作化成一樁痛苦之事,並公開宣稱他們的痛苦。但他們卻期望你能分享這種痛苦。
這真是個奇怪的矛盾,不是嗎?它聽起來充其量像清教主義。而我和你們相處感到快樂,作詩感到快樂,為我腦海產生的想法感到快樂。
正如我乘火車來時也感到快樂一樣。有一個晚上我半夜醒過來——我要說這件特別的事情了——我記得那個晚上我被人們關於“歡聚” ——這個可怕的詞“歡聚”——的談論攪得心煩意亂。這個詞鬼使神差地闖進我的腦海。
我不會為了那些事情而出去與人爭得你死我活。但我想到了雪萊——五六十年前的那個時候我正讀他的作品——(我一直沒有再讀他的作品,尤其在最近。他的一些作品我已爛熟心無需再看。)我想起了他的一首叫《阿拉斯特》的詩,並記起了本來忘得一干二淨的另一個標題。我沒意識到原來自己還記得它。但它確實在那夜閃入我的腦海。你們知道是什麼嗎?《阿拉斯特;遁世的精靈》。不是歡聚!
這是他筆下的一位詩人。我記得開頭部分:
有一位詩人英年早逝,他的墳
不是由虔誠的雙手敬重堆砌
而是打著漩渦的秋風魔法般地
使一座枯葉金字塔巍然聳立在
他腐爛的尸骨之上【……】
他如同棄兒獨自飄蕩在這個世界上,你們明白的,最後那樣死去。在那裡他將獨處到永遠。然而,他是位詩人。我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想到了這一點。(盡管我承認今晚我不是獨自一人。)然而,這些念頭就那樣進入了我的腦中。
我能記得——這本書中有一首我早期創作的詩歌——我能記得自己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大街上時,這首詩靈光一現的情形,那時由於聽說叔本華——(是聽說;在當時那個年紀我還沒有讀他的作品。我還在上高中。)聽說到他的思想,即這個世界——我們的世界,我的世界,你的世界,以及所有人的世界——都是我們的意志的產物。你們明白:世界作為意志……我的腦海裡反反復復思索著這句話。
我還記得當時在大街上具體位置。我思考著一件事:也許我自願存在於這個世界——我的存在是自身意志的表現。我也自願過我即將要過的無比糟糕的生活。這所有的一切在我出生前就已告知了我,也告知了許多其他人。人人都有機會擁有它,而我爭取到了它,開始投入生活。後來我又被提醒到:我不會再因為想到人生是出於自願的選擇,而產生安心之感。我被迫過完這一生——盡管我已經想不起——帶著對它的源頭的和未來的困惑過完這一生,盡管人生是一個我自己做出的選擇。
於是,我以此為素材寫下了一首相當長的詩,題目是“生存的艱難”。我仍然記得沿街行走時它閃現於腦海的時刻。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在作詩、談話、講課或者做別的事情時靈感一現的情形。
我常兩手空空走進很多課堂。我也不會把授課當做是授課。即使我一年隻上十二次課我也照樣領到薪水——在課堂上我會有類似的靈感湧現。那曾經讓我大為驚喜、情不自禁,特別想依此弄點東西出來。
記得在一所小小的鄉村高中時,我許多時刻都有這樣的想法。我記得許多日子,(雖然很多已經被我遺忘)——但是我能記得那些特別的日子,一些類似的事情讓我的生活充滿歌聲。
人們常常好奇,詩歌來自哪裡?我也完全不知道它們到底從何而來。但是那便是詩歌產生的地方之一。一種無可抗拒的巨大驚奇之饋贈,潛入我心間。
再給你們舉個例子吧。——(這個例子我偶爾纔這麼用。)——就在片刻之前我想到——如同那個夜晚一樣;漫步街頭,那個時刻;——我突然想到,縱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位在哲學領域聲名赫赫的女性。這聽起來是跟女性主義作對,不是嗎?其實不然。
柏拉圖,據我所知,說過哲學完全屬於雅典——存在於那一群民主主義者之中——智慧則屬於斯巴達。這些言論出自他的《普羅泰戈拉篇》,(這些都掠過我的腦海。)智慧,用其它的話說,在他看來,不是哲學。
現今,女人擁有智慧。但她們太過智慧反而不能成為哲學家。這就是對那句話的概括。(將來某天我會依此創作出一點東西,也許不一定寫成詩,可以寫一出戲劇。你們可以把它安排成三場戲然後寫出來。)
柏拉圖說過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本意並非說笑。我不記得他看起來好像知道自己在說笑。)——但他確實說了件有趣的事情。他說在斯巴達,當人們遇到智慧之神的顯現,並且開始對彼此說俏皮話,他們會將所有的陌生人逐出城邦,這樣他們就不會從自己身上學到什麼優點,例如此句諺語,“人生在世總會受一點委屈。”你們看,這就是智慧。這是智慧,可不是哲學。還有 “智者一言足矣。”諸如此類。
讓我們再來看看,“貓也可以打量國王。”你看,一些女人也許會這麼說。某些人過去不斷外出探訪或與人會面,然後回到家大談他或她——確切說是她——所見過的重要人士,一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就會說,“貓也可以打量國王。”在斯巴達也許就是這麼流傳的。
還有一個例子我已經舉過,它好像來自斯巴達,“好籬笆纔有好鄰居。”(22)這是個很老很老的說法了,我沒有借此創作出什麼,不過我倒希望我這麼做了。
這就是我說的“智慧”,不是“哲學”。哲學涉及泰勒斯和亞歷山大以及這一類的人或事,——斯賓諾沙以及與之有關者。它有著重要的地位——(我得小心一點,也許觀眾裡面就坐著一兩位哲學家)——它的重要地位有如宗教,占據、淨化、洗滌人們的思想。
所有的哲學都與萬能的上帝的問題有關。它試圖去淨化。它的目的是洗淨宗教裡小部分比較嚴重的封建迷信,在這點上它並非徒勞無功。
但你們看,宗教是非常具有女性特征的。在哲學領域,我們知道的唯一一位女性就憎惡宗教。她的名字是贊西佩。她厭惡宗教;當哲學家門在她窗外高談闊論時,她就朝他們潑髒水。這可是一個事實,不爭的事實,歷史上有記載。
然後再談談科學,這可是比你們意識到的更加具有女性特征。所有的科學都是關於家庭的科學——都涉及人在這個星球上居住和我們對其的占有。至於實驗室,它們無非就是貼了金的廚房。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智慧存在在哪裡,它來自具有洞見的諺語,和對生活的揭示,大部分來自“閑聊”——來自我們彼此間的普通交談,相互猜測。我們常常猜測著彼此:“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我們猜測著事情的原委。“那兩個人的頭緊緊挨在一起,是有什麼事在發生嗎?”
閑聊,搖身成為雜志;接著成為編年史;進而升級成為歷史;再接著成了戲劇和文學;最終到達詩歌的階段。但是這個結局太令人沮喪,它充滿女性色彩——應該既和女人有關,又和男人有關。
宗教的結局,也同樣非常具有女性色彩,你們知道的。你們隻要想想夏娃和聖母瑪麗亞——(你看,兩位都是女士)還有維納斯;這三位讓宗教非常具有女性色彩。這真是個女性的談話,你們看——正發生在我身上。
以上就是這些想法的產生過程的展示。我此刻正在進行的講話,這自由的,輕松的又具有影響的談話,也許有一天就成為了一首長詩。
我的初衷幾乎已經奇妙地達到了。你們知道,我仍然是位教授,今晚,在這裡教書。(在這樣一個大教室)一直以來,我越來越深地意識到我的願望已經實現,那就是我一年隻教授十節,十五節,或者二十節的課。
我想說,並不是每一節課都是呈現新穎的觀點。我能用一種變化著的理念——隨著它的變化——在這變化之中,我可以用三次。所以,二十一除以三就是一年七次課。我猜是二十一節,或者在這左右吧。
現在,詩歌必須與現實生活全面關聯。詩中總有一個核心句子來自生活中的瑣碎言語所包含的洞見之一,也就是智慧。詩歌若不具有這樣微妙的聯繫,我就認為它不存在價值。
讓我們選一個詩句為例。這詩句是,“地球是愛的如意居所。”它出自我創作的詩歌之一。我待會兒再來說這整首詩歌。“地球是愛的如意居所:/我不知道它還可能去哪個更好的地方,”我如此寫道。在我開始寫詩時,我並不知道我會寫出這種句子。但我記得那靈光一現的詩意正來自龐雜的生活。
像這樣的短小詩句都是從龐雜的生活升華而來。對於一些人來說這非常難以理解。它看上去如此簡單和短小。但它的成功之處在於,這簡短的詩行凝結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多少快樂和痛苦。【……】
[弗羅斯特先生說的是他的詩歌“白樺林”。]
你們注意,詩歌中的這兩句,大概就是上帝差遣我寫詩的原因——繆斯指使我寫詩的原因——讓我下筆自成詩行,“在我正對斟酌頗感疲憊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就將它寫入詩行,但冥冥之中就寫了進去。另外一句是,“地球是愛的如意居所:/我不知道它還可能去哪個更好的地方。”
這就是我想說的全部,閑聊和故事——一次閑聊;聊聊天;講講故事。這就是閑聊;自然的閑聊。
……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在詩人晚年的時候,曾有那麼一次,他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對自己一次演講的全面修改中。這次演講他為獲得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頒發的愛默生-梭羅獎章而做的,時間是1959年。他講的是愛默生,一位他內心極為敬佩的人。他的演講重點,毫無疑問,是他對特別崇敬者的評價。
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表演——“表演”這個詞,並不是隨意撚來的,在大家使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他之前,他就是“一位表演藝術家”——他的表演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也能給大家帶來聽覺享受。恰如庫克在1956年題為“作為教師的弗羅斯特”所言:“說話,當然是演講最主要的構成要素,”總是伴隨著各種手勢、頻頻點頭、面部表情的不斷變化,甚至腳上的步伐。(所有這些也都根據聽眾的感覺而移動,一會兒靠向他們,一會兒又後退幾步。)聲音、手勢、表情、著裝——所有這些人性化的考慮都是那麼自然得體,令人印像深刻。弗羅斯特一貫言行一致。在他身上,你永遠看不到一個矯飾詩人的影子,也永遠聽不到不是詩人的聲音。
他的聽眾,無論多和少,都十分清楚,他們在親身感受一位重要人物的“自然表現”。而這種在演說者和聽眾兩者之間的共識,形成了最初的聯結。這種聯結在每一個演講會結束之時,都會把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由於弗羅斯特總是要求把演講大廳的燈打開,以便他能清晰地看到聽眾的表情,所以這種聯結被強化了。
當他在對聽眾發表演說時,他總是欲言又止,常常又非常謙卑。他經常在演說中間插入一些旁白。他說話的速度隨著自己思考的速度而調整。在這個方面,彼得?斯丹利斯曾參加過詩人多種場合的演講,也是詩人的好友,他在為詩人的《弗羅斯特百年文集》其中一卷中如此寫道:“他總是給人這樣的印像:從一點到另一點,乃至從一個短語到另一個短語,他總在思考、即興地調整,而顯然詩人又在不斷挖掘內心的東西,希望能從內心深處被遮蔽的某地尋找到一個原創的觀念、意像、抑或是類比,但是當這些觀念、意像、類比在他內心湧現出來並通過他的嘴說出來時,從說出的過程也能明顯地看出詩人在努力尋找直接向每位聽者表達的準確詞彙和聲調。這一切,都真切地反映在他的手勢和面部表情中。”
伴隨著這種融洽的氛圍、復雜的思想和信手撚來的慣用語,詩人常常運用一些方言,把“because”縮讀為“cause”或者“them”讀為“em”或者把“so as”讀為“so’s”——或者說“gotta”“tis”“tis’nt”等。為了效果,他有時直接使用分明是俚語的表述,如“That don’t mean……”,“Ain’t it hell……”
簡而言之, 他的風格就是一種談話式的。因為談話是一種聽覺媒介,而不是書寫媒介——當與談話對像面對面時,也是一種視覺媒介——因而弗羅斯特談話的真實文本,以及他談話的整體效果,根本無法完全捕獲,在書寫文本中不得不有所遺漏。馬克?吐溫在一百年前在口述自傳中所談的完全正確。漫談編輯毫無疑問常常有機會遭遇這種情況,在這方面,弗羅斯特在六十年前的談論修訂時就說了:“我沒有直接清晰表達我的觀點,這很讓人沮喪。”
作為一位把談話內容編輯成為文本並出版的編者,他不可能到處都加括號添注釋(如給演員的對話腳本那樣)說明什麼是怎麼被說的:認真的,隨意的,玩笑似的,等等。一個清楚的例證來自於本選集一個演講,那是詩人1956年應邀在俄勒岡大學做的演說,這是一個很容易被誤解誤釋的表述。在他評論的開始,他非常簡略地談到他的教書哲學,以及寫作哲學,然後他補充了一些話,這些話對讀者好像有點古怪、刺耳:“說起那些各式各色人們,他們裝得像我一樣重要,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這個例子,以及其他很所例子,文字稿根本無法復制說話時的情景,包括語調與臉部表情,而那個四月旁晚在尤金的聽眾都清楚明白詩人這隻是一句詼諧的自嘲話。
以印刷文本的方式也根本無法完全展示弗羅斯特演說時的幽默方式。1960年詩人的一次演說(也包括在本書中)中,詩人與他的一位有點醉意的詩友互嘲——詩人模仿詩友含糊不清的說話(“我模仿他說話的方式”),帶給聽眾無比的歡樂——但在文本中無法展示。
本書後面選取的是詩人弗羅斯特在三十二個學校的四十六次演說,時間跨度從1949到1962年,也就是詩人人生最後的十四年。其中,詩人在達特默思(馬薩諸塞州南部一個鎮——譯者注)做的演說數量最多,部分原因是那時詩人在每年學院著名的大講壇之前都會出現在那兒,而所有演講都會被錄音。盡管錄音後來變得很普遍,但在當時,其他地方卻是比較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羅斯特的演說每每總是征引很多其他詩人的詩句,包括英國和美國的詩人,而他的征引完全是憑記憶,且準確度很高。讀者在後面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詩人會在逐字背誦詩句時偶有疏忽。(在1955年七月一次與面包英語學校的學生談話中,他問道:“有些詩句沉入你的記憶,與你完全融為一體,最後它發生了某種變異,你們曾經注意到這種情況嗎?”)
偶爾,詩人對自己寫的詩句也會支吾其詞,甚至連他非常熟悉的詩歌“樺樹”也是如此——1955年他在國會圖書館告訴聽眾:“我完全能背誦,我對它太熟悉,有時我在中間就忘記了……上次我說這詩時就說錯了。”他也熟悉愛默生的詩歌,但有時他也把“給予愛一切”這首詩的最後一節開頭“Heartily know……”說成了“Verily know……”
另外,他有時在談到相關出版物的題目時也有遺忘或者不夠嚴謹,這在後面的文稿中會有不少地方出現:把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窮》變成了《貧窮與進步》,把“聯邦論”變成了“聯邦論文”,把“空心人”(原文是Hollow Men——譯者)變成了“空心人”(原文是Hollow Man——譯者)。引用他自己的詩歌也免不了疏漏,如把“The Tuft of Flowers”誤引為“A Tuft of Flowers”。(意思是“花簇”,把定冠詞“the”誤以為不定冠詞“a”——譯者注) 所有這些都不會有很嚴重的後果——對他似乎如此,對他的聽眾當然更是如此。
本書收錄的弗羅斯特演講詞內容豐富,有的是關於詩人自己的,有的是關於詩歌的,有的是關於生活的,而有的則是關於詩人、詩歌與生活幾者之間相互關聯的。當然,這些演講詞最重要的是,顯示出弗羅斯特是一位職業詩人,但是從最根本而言,弗羅斯特在作為一名職業詩人的同時,身上又總是展示出一位教師的稟賦。在弗羅斯特身上,我們看到了教師和詩人兩種身份的完美結合,這在他的詩作和公眾演說中表現出來——在他的詩歌朗讀和與聽眾漫談中——特別是在大學校園裡,這兩者結合的更是相當完美。詩人與教師,在弗羅斯特是須臾不可分離的。
“在我看來,教師的任務,就是挑戰學生的目標”。弗羅斯特在接受采訪時如是說,在采訪中他把自己的教學方法描述為“言傳身教”,該采訪刊載在1925年11月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無論對於那些深入研究或者僅僅草草閱讀本書的讀者而言,他的這種描述和定位都具有啟示意義。)“我並不是說,這種挑戰是言語的。”他解釋到,“僅僅從言語層面的挑戰是無益的”。他進一步明確指出:“……我是一位冷漠的老師,就像一般教師一樣。很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大學生需要我,隻能說明我來到他們中間能釋放出某種力量。肯定是我所做的非常奏效。”
1956年的一個下午,詩人在哈佛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本選集有摘錄),他談到了自己的生活與談話及教育的關繫,並引用了自己創作的兩行詩:“需要各種家庭及社會的教育/纔能適應我的那種詼諧”。弗羅斯特的多數詩歌都是以戶外為背景的,而他幾乎所有的教學都在室內。要全面認清弗羅斯特,讀者需要從室外來考察來考察室內的他。從這個方面來說,弗羅斯特在學院、大學、小學教室及演講廳給予了我們的真知灼見,比在其他任何室內的地方都要多得多——在這些地方詩人多年來詩人面對難以數計的學子以及他非常喜歡的城鎮市民發表演說。
在1951年《大西洋月刊》發表的題為“詩歌與學校”的雜記中,詩人有兩個句子結合了他的“室內天纔”與“室外天纔”,這兩句至今對我們仍有啟示意義:“教育得最好的人,是一位成熟到恰到好處的人。沒有水分但並沒有干枯。”這裡選錄的弗羅斯特以前沒有公開出版的演說詞,有的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流逝,應該可以說是成熟到恰到好處了。翻閱這部書,你會發現:它們已經沒有水分,但是並沒有干枯。
查看全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