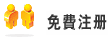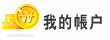譯後記
布羅茨基的《小於一》,陪伴我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我時不時會冒出一個念頭:我應該譯這本書。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自我推薦的念頭:這本書應該由我來譯。現在,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在20世紀重要的詩人批評家中,我喜愛的是瓦萊裡、艾略特、曼德爾施塔姆、奧登、布羅茨基、希尼。當然,還得加上“詩人批評家”形像不那麼鮮明但可能更值得挖掘和細味的葉芝和米沃什,他們的詩論和文論都夾雜在他們眾多的散文隨筆中,他們的批評都超出文學範圍,探討宗教和哲學問題——當然,作為葉芝的後輩,艾略特和奧登的批評也都指涉這些問題。
布羅茨基這本《小於一》置於這些大師的批評著作之中,其特別令我著迷和心儀之處是他的文體,以及這本書的“書體”。他文章的語調,近於中立,並且由於他自稱寫英語是為了“取悅一個影子”也即取悅奧登,因此還很克制和謙遜,而謙遜在本質上是自信——或者反過來說,我們首先聽到的是自信,並發現它其實是謙遜——這使得他的語調特別有說服力,進而使得他的眼界,或者說真知灼見,在這語調的控制下光芒四射。
至於這本書的“書體”,我認為它無論是作為一本作家隨筆集,還是作為一本詩人批評家的隨筆集,都是獨一無二和無可匹比的。首先,它不是一部純粹的批評著作,也即不是純粹的批評文章結集或專著,而是結合了自傳成分,而由於布羅茨基的經歷極具傳奇性,因此這自傳成分不僅包含了對詩歌的評論,還有對社會和政治的評論,尤其是對極權制度的評論。而我個人認為,散見於布羅茨基文章中的這些評論,是特別值得中國讀者尤其是中國作家重視的。我說“評論”而不說“抨擊”,必須解釋一下。布羅茨基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他本人已在美國,但是他絕不像大多數流亡者那樣利用或推廣自己的流亡身份,以此撈取無論是什麼好處,包括名與利。相反,他盡可能地淡化自己的經歷(是的,與他的俄羅斯詩歌前輩們的經歷相比,他算得了什麼呢),而且深入語言和詩歌內部,並從那裡發來報道,包括——尤其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俄羅斯那些聖徒、烈士似的現代詩人。他原可以用公共語言和措辭大肆抨擊那個政權,但是他不屑於這樣做,而僅僅是或常常是在談論自己的成長和談論詩歌或詩人時順便一提,略加評論,這反而使他的評論更具深度和洞察力。他這種不屑,不是一般的傲慢姿態,而是“一個詩人對一個帝國”的高度。而這個高度,又源自於他的一個信念,認為語言高於一切,甚至是時間崇拜的對像,而詩歌是語言的形式。
其次,這是一部以長篇文章為主的隨筆集,夾以若干短文,原書五百頁,僅十八篇文章,其目錄剛好占一頁。除了標準的“詩人批評家”的長篇文章例如評論阿赫瑪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萊、曼德爾施塔姆夫婦、沃爾科特、茨維塔耶娃和奧登的文章外,還有幾篇短則三四十頁、長則五六十頁的“超文章”,包括分別對茨維塔耶娃和奧登各一首詩的細讀;對20世紀俄羅斯散文(主要指小說)的無情裁決(《空中災難》);對自己的成長(《小於一》)、對父母(《一個半房間》)和對他的城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的回憶;以及歷史筆記和遊記(《逃離拜占庭》)。如果說布羅茨基在長篇文章中展示了其視力和能力的話,《論獨裁》和《畢業典禮致詞》這兩篇短文則證明他同樣有過人的濃縮和壓縮能力,也證明他在探討詩歌、語言問題和順便對社會制度略作評論之外,同樣可以單刀直入地批評獨裁政權和剖析善惡。而另一篇短文《自然力》則以真正“隨筆”的方式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實上,我建議初次接觸布羅茨基的讀者先讀這三篇短文,不是作為開胃小菜,而是接受當頭棒喝。
布羅茨基這本書中的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我所稱的文體和“書體”的獨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書。相對而言,他的另一本篇幅相當的隨筆集《悲傷與理智》盡管是一流的,也是任何布羅茨基讀者不能錯過的,但其“書體”就不像《小於一》化和綜合化,而更像一本標準的詩人批評家隨筆集。但我得說,即使是我這樣的布羅茨基迷,在初讀《小於一》中的三篇“超文章”《論奧登的〈1939年9月1日〉》《一首詩的腳注》和《逃離拜占庭》時,還是會覺得冗長而煩瑣。但根據我多次通讀和校對譯文的經驗,這三篇文章是值得細嚼的,隻要你付出耐性,一定會有回報。例如《逃離拜占庭》,一方面是歷史筆記,一方面是遊記,可以說是無文學味的,詩歌和文學讀者可能會不太感興趣,但是文章中布滿各種奇思妙想和犀利洞察,你在其他關於歷史的文章和遊記中是踫不到的。
總之,我個人認為,布羅茨基這本《小於一》是20世紀好的隨筆集,而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批評家的隨筆集。任何讀者都可從這本書中獲得很多東西,不僅可作為文學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參照繫,而且可作為一個高標準,來衡量自己和別人寫作的斤兩。至少,受到這本書的洗禮,我們就不會對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還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過在意,這可省去我們很多時間。
這本書的翻譯頭頭尾尾耗時兩三年,其間譯者經歷了離婚、父親逝世、賣房子、搬家,從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崗位上辭職,再從香港遷居深圳等人生重大變故,仿佛譯者也必須以實際行動對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不過,我認為應該反過來說纔對,是翻譯和漫長的校對工作幫助我度過這些原應是艱難的時刻。
趁這次再版,我要感謝為本書初版付出努力和提供有益建議的曹潔女士、郭賢路先生和喬直先生。這次再版,我對一些用詞作了修訂,對一些錯誤作了糾正。後也是重要的,特別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宋僉先生重新做了細心的、水平極高的校對,糾正了不少錯誤。
譯者,2020年11月18日,深圳洞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