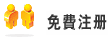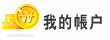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於無色處見繁花》是張曉風執筆五十年的生命感悟。張曉風用敏感纖細的心靈感應自然和人生,在清風明月、山松野草之間馳騁,又在馳騁中追懷往事、思憶故人,並親自作序提醒讀者:在庸常的世界裡,發現細微的美好。
《拎起寂寞的影子》是大陸首次出版的一部林清玄記錄紅塵之作。全書細膩描摹臺灣鄉村風土人情和城市社會變革的作品集,是讀者了解臺灣百姓生活的一部重要著作。
《孤獨的靈魂,當慣於遠征》是餘光中經典散文集。孤獨的靈魂,漫漫的遠征,貫穿了餘光中近一個世紀的漂泊旅程,令讀者強烈感受到其濃濃的鄉愁,以及對中華傳統語言文字的深度繼承和完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