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20世紀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生於俄國猶太家庭,1921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哲學,1957年就任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發表具有開創性的“兩種自由概念”演說,同年獲封爵士。作為傑出的觀念史學家和學科主要奠基人,先後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和伊拉斯謨獎。主要著作有《自由論》、《俄國思想家》《反潮流》《個人印像》《扭曲的人性之材》《現實感》《浪漫主義的根源》《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蘇聯的心靈》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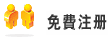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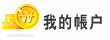  |
[ 收藏 ] [ 简体中文 ] |
| 臺灣貨到付款、ATM、超商、信用卡PAYPAL付款,4-7個工作日送達,999元臺幣免運費 在線留言 商品價格為新臺幣 | |














